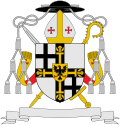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
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пјҲеҫ·иӘһпјҡDeutscher OrdenпјҢDeutschherrenorden жҲ– Deutschritterorden[1]пјӣиӢұиӘһпјҡTeutonic OrderпјүпјҢеҸҲиҜ‘еҫ·ж„Ҹеҝ—йЁҺеЈ«еңҳ[иЁ» 1]пјҢжӯЈејҸеҗҚз§°дёә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ңЈзҺӣеҲ©дәҡеҢ»йҷўеҫ·ж„Ҹеҝ—е…„ејҹйӘ‘еЈ«еӣўпјҲжӢүдёҒиӘһпјҡOrdo domus Sanctae Mariae Theutonicorum Ierosolimitanorumпјӣеҫ·иӘһпјҡOrden der BrГјder vom Deutschen Haus Sankt Mariens in JerusalemпјүпјҢдёҺеңЈж®ҝйӘ‘еЈ«еӣўгҖҒеҢ»йҷўйӘ‘еЈ«еӣўдёҖиө·е№¶з§°дёәдёүеӨ§йӘ‘еЈ«еӣўгҖӮе…¶дҪңзӮәдёҖеҖӢеӨ©дё»ж•ҷжңғжүҖе»әз«Ӣзҡ„и»ҚдәӢдҝ®жңғгҖӮ 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иө·жәҗеҸҜиҝҪжәҜиҮізәҰ1190е№ҙ第дёүж¬ЎеҚҒеӯ—еҶӣдёңеҫҒжңҹй—ҙпјҢз”ұдёҚжқҘжў…дёҺеҗ•иҙқе…Ӣзҡ„е•ҶдәәеңЁеңЈең°йҳҝе…ӢпјҲд»Ҡд»ҘиүІеҲ—йҳҝеҚЎпјүеӣҙеҹҺжҲҳдёӯе»әз«Ӣзҡ„йҮҺжҲҳеҢ»йҷўгҖӮ1199е№ҙ2жңҲ19ж—ҘпјҢж•ҷе®—иӢұиҜәжЈ®дёүдё–жү№еҮҶе°ҶиҝҷдёҖж–ҪжөҺеӣўдҪ“иҪ¬еҸҳдёәйӘ‘еЈ«дҝ®дјҡпјҢ并е°ҶеҢ»йҷўйӘ‘еЈ«еӣўдёҺеңЈж®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дҝ®дјҡ规еҲҷиөӢдәҲиҜҘвҖң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ңЈзҺӣеҲ©дәҡеҫ·ж„Ҹеҝ—дәәд№Ӣ家вҖқ[2][иЁ» 2]гҖӮ 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13дё–зәӘйҖҗжӯҘд»Һиө·еҲқзҡ„ж…Ҳе–„еӣўдҪ“жј”еҸҳдёәеҶӣдәӢ-е®—ж•ҷз»„з»ҮпјҢжҙ»и·ғдәҺзҘһеңЈзҪ—马еёқеӣҪгҖҒеңЈең°гҖҒең°дёӯжө·ең°еҢәд»ҘеҸҠзү№е…°иҘҝз“Ұе°јдәҡпјҢеңЁеҹәзқЈеҫ’иў«з©Ҷж–Ҝжһ—й©…йҖҗеҮәеңЈең°еҗҺ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иҪ¬з§»иҮідәҶжіўзҪ—зҡ„жө·жІҝеІёпјҢ并еҸӮдёҺдәҶеҫ·ж„Ҹеҝ—дәәзҡ„дёңеҗ‘ж®–ж°‘жү©еј гҖӮиҝҷдёҖеҸ‘еұ•еӮ¬з”ҹеҮәеӨҡдёӘй©»ең°пјҢе…¶еӯҳз»ӯж—¶й—ҙдёҚдёҖгҖӮиҮӘ13дё–зәӘжң«иө·пјҢеңЁжҷ®йІҒеЈ«ең°еҢәе»әз«Ӣзҡ„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ӣҪйҖҗжёҗжҲҗдёәж ёеҝғгҖӮеҲ°14дё–зәӘжң«пјҢиҜҘйӘ‘еЈ«еӣҪ家зҡ„йўҶеңҹйқўз§ҜиҫҫеҲ°дәҶ20дёҮе№іж–№е…¬йҮҢгҖӮ[3] 然иҖҢ1410е№ҙеӨҸеӯЈ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з¬¬дёҖж¬ЎеқҰиғҪе ЎжҲҳеҪ№дёӯйҒӯеҲ°жіўе…°-з«Ӣйҷ¶е®ӣиҒ”еҶӣзҡ„йҮҚеӨ§еҶӣдәӢжү“еҮ»пјҢд»ҘеҸҠ15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дёҺжҷ®йІҒеЈ«еҪ“ең°дәәд№Ӣй—ҙж—·ж—ҘжҢҒд№…зҡ„еҶІзӘҒпјҢеҠ йҖҹдәҶйӘ‘еЈ«еӣўеҸҠе…¶ж”ҝжқғиҮӘ15дё–зәӘеҲқд»ҘжқҘзҡ„иЎ°иҗҪгҖӮ1525е№ҙпјҢйҡҸзқҖе®—ж•ҷж”№йқ©зҡ„жҺЁиҝӣпјҢеү©дҪҷзҡ„йӘ‘еЈ«еӣўеӣҪиў«дё–дҝ—еҢ–пјҢж”№еҲ¶дёәдёҖдёӘдё–дҝ—е…¬еӣҪпјҢиҮӘжӯӨ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жҷ®йІҒеЈ«еҸҠ1561е№ҙеҗҺзҡ„еҲ©жІғе°јдәҡеӨұеҺ»е®һиҙЁеҪұе“ҚеҠӣгҖӮ然иҖҢеңЁзҘһеңЈзҪ—马еёқеӣҪеўғеҶ…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ңЁеҫ·еӣҪеҚ—йғЁгҖҒеҘҘең°еҲ©е’Ңз‘һеЈ«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д»ҚжӢҘжңүеӨ§йҮҸең°дә§е№¶жҢҒз»ӯеӯҳеңЁгҖӮ 18дё–зәӘжң«еӣ еҸҚжі•еҗҢзӣҹжҲҳдәүеӨұеҺ»иҺұиҢөжІіе·ҰеІёйўҶең°пјҢд»ҘеҸҠ19дё–зәӘеҲқеңЁиҺұиҢөйӮҰиҒ”еҗ„йӮҰзҡ„дё–дҝ—еҢ–ж”№йқ©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жүҖжңүең°дә§иў«еүҘеӨәпјҢд»…еү©еҘҘең°еҲ©еёқеӣҪеўғеҶ…зҡ„дә§дёҡеҫ—д»Ҙдҝқз•ҷгҖӮиҖҢиҝҷдәҰйҡҸзқҖ第дёҖ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ҳеҗҺеҘҘеҢҲеёқеӣҪи§ЈдҪ“еҸҠ1919е№ҙ4жңҲеҘҘең°еҲ©зҡ„иҙөж—ҸеәҹйҷӨжі•йўҒеёғ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дёҚд»…еӨұеҺ»дәҶеӨ§йҮҸең°дә§пјҢе…¶йӘ‘еЈ«еұһжҖ§дәҰдёҚеӨҚеӯҳеңЁгҖӮиҮӘ1929е№ҙиө·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з”ұзҘһзҲ¶еӣўдҪ“йўҶеҜјпјҢдҫқз…§гҖҠж•ҷдјҡжі•гҖӢиў«и®Өе®ҡдёәзҘһиҒҢдҝ®дјҡгҖӮ[4] 19дё–зәӘеҸҠ20дё–зәӘдёҠеҚҠеҸ¶зҡ„еҺҶеҸІеӯҰз ”з©¶дё»иҰҒйӣҶдёӯдәҺиҜҘ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жіўзҪ—зҡ„жө·ең°еҢәзҡ„йӘ‘еЈ«ж”ҝжқғпјҢжҷ®йҒҚе°Ҷ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дёҺйӘ‘еЈ«еӣўеӣҪи§ҶдёәдёҖдҪ“гҖӮеҫ·гҖҒжіўгҖҒдҝ„дёүеӣҪеҜ№йӘ‘еЈ«еӣўеҺҶеҸІзҡ„з ”з©¶дёҺи§ЈиҜ»еӯҳеңЁжҳҫи‘—е·®ејӮпјҢеёёеёҰжңүејәзғҲзҡ„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жҲ–еӣҪ家主д№үиүІеҪ©гҖӮзӣҙиҮідәҢжҲҳз»“жқҹеҗҺпјҢеӣҪйҷ…еӯҰз•ҢжүҚејҖе§Ӣзі»з»ҹгҖҒж–№жі•и®әжҖ§ең°з ”究иҜҘ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ҺҶеҸІдёҺз»“жһ„гҖӮ[5]зҺ°ж—¶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ҸЈеҸ·жҳҜвҖңеё®еҠ©гҖҒе®ҲеҚ«гҖҒж•‘жІ»пјҲеҫ·иӘһпјҡHelfen, Wehren, HeilenпјүвҖқпјҢзёҪйғЁиЁӯж–јз¶ӯд№ҹзҙҚгҖӮ еҗҚз§°и©Іж•ҷеӣўзҡ„еҺҹеҗҚдёә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ңЈзҺӣдёҪдәҡеҢ»йҷўеҫ·ж„Ҹеҝ—е…„ејҹйӘ‘еЈ«еӣўпјҲеҫ·иӘһпјҡOrden der BrГјder vom Deutschen Haus St. Mariens in Jerusalem жҲ– жӢүдёҒиӘһпјҡOrdo domus Sanctae Mariae Theutonicorum HierosolymitanorumпјүгҖӮжўқй “пјҲTheutonicorumпјүдёҖи©һеҸҚжҳ дәҶ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ҫ·ж„Ҹеҝ—иө·жәҗпјҢеңЁжұүиҜӯе’ҢиӢұиҜӯдёӯд№ҹеёёд»ҘжӯӨиҜҚжҢҮд»ЈиҜҘйӘ‘еЈ«еӣўгҖӮдҪҶиҲҮжўқй “дәәжҜ«з„Ўй—ңдҝӮ[6]гҖӮ еңЁеҫ·иҜӯиҜӯеўғдёӯ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иў«з§°дёәеҫ·ж„Ҹеҝ—йӘ‘еЈ«еӣўпјҲеҫ·иӘһпјҡDeutscher OrdenпјүпјҢжӯ·еҸІдёҠд№ҹжӣҫиў«з§°дёәеҫ·ж„Ҹеҝ—йӘ‘еЈ«еӣўпјҲеҫ·иӘһпјҡDeutscher Ritterorden жҲ– DeutschritterordenпјүгҖҒеҫ·ж„Ҹеҝ—йўҶдё»еӣўпјҲеҫ·иӘһпјҡDeutschherrenordenпјүгҖҒзҺӣдёҪдәҡзҡ„йӘ‘еЈ«пјҲеҫ·иӘһпјҡMarienritter)гҖҒзҷҪиўҚйўҶдё»еӣўпјҲеҫ·иӘһпјҡDie Herren im weiГҹen MantelпјүзӯүгҖӮ еңЁдёңеҢ—欧жӣҫз»Ҹе’ҢйӘ‘еЈ«еӣўеҸ‘з”ҹжҲҳдәүзҡ„еӣҪ家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иў«зЁұзӮәеҚҒеӯ—йӘ‘еЈ«еӣўпјҲжіўиҳӯиӘһпјҡZakon KrzyЕјackiпјҢж„ӣжІҷе°јдәһиӘһпјҡSaksa Orduпјӣз«Ӣйҷ¶е®ӣиӘһпјҡKryЕҫiuoДҚiЕі OrdinasпјӣжӢүи„ұз»ҙдәҡиҜӯпјҡVДҒcu OrdenisпјүгҖӮ йҰ¬е…ӢжҖқзҡ„дёҖд»ҪжүӢзЁҝжӣҫ經е°ҮжқЎйЎҝйЁҺеЈ«еңҳжҸҸз§°дёә ReitershundeвҖ”вҖ”ж„ҸжҖқжҳҜвҖңдёҖеӨ§зҫӨйЁҺеЈ«вҖқпјҢ然иҖҢеҪ“д»–зҡ„д№ҰиҜ‘д»ӢиҮідҝ„еӣҪж—¶пјҢиҜ‘иҖ…е°ҶйҖҷеҖӢзҹӯиӘһеҫһеӯ—йқўдёҠзҝ»иӯҜзӮәвҖңзӢ—йЁҺеЈ«вҖқпјҲРҹСҒСӢ-СҖСӢСҶР°СҖРёпјҢжқҘиҮӘ Reiter HundeпјүпјҢйҖҷеңЁдҝ„иӘһдёӯжҲҗзӮәдәҶдёҖеҖӢжҷ®йҒҚзҡ„гҖҒиІ¶зҫ©зҡ„жЁҷзұӨгҖӮ1938е№ҙи¬қзҲҫи“ӢВ·ж„ӣжЈ®ж–ҜеқҰжҸҸиҝ°1241е№ҙеҶ°ж№–д№ӢжҲҳзҡ„еҸҚеҫ·йӣ»еҪұгҖҠдәһжӯ·еұұеӨ§В·ж¶…еӨ«ж–ҜеҹәгҖӢдёҠжҳ д№ӢеҫҢпјҢжӯӨз§°е‘јеҸҳеҫ—жӣҙеҠ жөҒиЎҢиө·жқҘгҖӮ еҺҶеҸІйЁҺеЈ«еңҳжҲҗз«Ӣд№ӢеүҚзҡ„е…„ејҹжңғж–ј1191е№ҙз”ұдҫҶиҮӘдёҚдҫҶжў…е’Ңе‘ӮиІқе…Ӣзҡ„еҫ·ж„Ҹеҝ—е•ҶдәәеңЁйҳҝеҚЎжҲҗз«ӢгҖӮеңЁдҪ”й ҳйҳҝеҚЎеҫҢпјҢд»–еҖ‘жҺҘз®ЎдәҶи©ІеёӮзҡ„дёҖ家йҶ«йҷўдҫҶз…§йЎ§з—…дәәпјҢдёҰй–Ӣе§Ӣе°ҮиҮӘе·ұжҸҸиҝ°зӮә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ҫ·ж„Ҹеҝ—д№Ӣ家зҡ„иҒ–з‘Әйә—йҶ«йҷўгҖӮдёҚд№…пјҢж•ҷе®—е…ӢиҗҠеӯҹдёүдё–жү№еҮҶдәҶе®ғ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й–Ӣе§ӢеңЁOutremerпјҲеҚҒеӯ—и»ҚеңӢ家зҡ„зёҪзЁұпјүдёӯзҷјжҸ®йҮҚиҰҒдҪңз”ЁпјҢжҺ§еҲ¶и‘—йҳҝеҚЎзҡ„жёҜеҸЈйҖҡиЎҢиІ»гҖӮеҹәзқЈж•ҷи»ҚйҡҠеңЁдёӯжқұиў«ж“Ҡж•—еҫҢ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ж–ј1211е№ҙ移иҮізү№иҳӯиҘҝз“Ұе°јдәһпјҢд»Ҙ幫еҠ©дҝқиЎӣеҢҲзүҷеҲ©зҺӢеңӢзҡ„жқұеҚ—йӮҠз•Ңе…ҚеҸ—еә«жӣјдәәзҡ„ж”»ж“ҠгҖӮ1225е№ҙпјҢеҢҲзүҷеҲ©еңӢзҺӢе®үеҫ·йӯҜдәҢдё–и©Ұең–еңЁзү№иҳӯиҘҝз“Ұе°јдәһеўғе…§е»әз«ӢиҮӘе·ұзҡ„еңӢ家пјҢиҖҢж•ҷзҡҮеҘ§и«ҫйҮҢзғҸж–Ҝдёүдё–зҡ„ж•ҷзҡҮи©”жӣёиҒІзЁұйЁҺеЈ«еңҳеңЁзү№иҳӯиҘҝз“Ұе°јдәһзҡ„й ҳеңҹеҫҢ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иў«жӯҰеҠӣй©…йҖҗгҖӮ 1230е№ҙпјҢйҮҢзұіе°јзҡ„йҮ‘зҺәиҜҸд№ҰеҸ‘еёғпјҢеӨ§еӣўй•ҝиө«зҲҫжӣјВ·йҰ®В·иҗЁзҲҫжүҺе’ҢйҰ¬зҙўз¶ӯдәһе…¬зҲөеә·жӢүеҫ·дёҖдё–зҷјиө·дәҶжҷ®йӯҜеЈ«еҚҒеӯ—и»ҚжқұеҫҒпјҢиҒҜеҗҲе…Ҙдҫөжҷ®йӯҜеЈ«пјҢж—ЁеңЁе°Үжіўзҫ…зҡ„жө·еҸӨжҷ®йӯҜеЈ«дәәеҹәзқЈж•ҷеҢ–гҖӮйЁҺеЈ«еҖ‘иҝ…йҖҹжҺЎеҸ–жҺӘж–Ҫе°ҚжҠ—д»–еҖ‘зҡ„жіўиҳӯжқұйҒ“дё»пјҢдёҰеңЁзҘһиҒ–зҫ…йҰ¬еёқеңӢзҡҮеёқзҡ„ж”ҜжҢҒдёӢпјҢе°ҮеҸ—жіўиҳӯе…¬зҲөйӮҖи«Ӣзҡ„жө·зғҸе§Ҷи«ҫең°пјҲд№ҹзЁұзӮәйҪҠзұідәһВ·еҲҮзғҸжҳҺж–ҜеҚЎжҲ–еә«зҲҫй»ҳиҳӯпјүзҡ„ең°дҪҚж”№и®ҠзӮәд»–еҖ‘иҮӘе·ұзҡ„иІЎз”ўгҖӮеҫһйӮЈиЈЎй–Ӣе§Ӣ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еүөе»әдәҶзҚЁз«Ӣзҡ„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дҝ®йҒ“йҷўеңӢпјҢдёҚж–·еўһеҠ иў«еҫҒжңҚзҡ„жҷ®йӯҜеЈ«дәәзҡ„й ҳеңҹпјҢйҡЁеҫҢеҫҒжңҚдәҶ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гҖӮйҡЁи‘—жҷӮй–“зҡ„жҺЁз§»пјҢжіўиҳӯеңӢзҺӢиӯҙиІ¬йЁҺеЈ«еңҳ沒收他еҖ‘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зү№еҲҘжҳҜеә“е°”е§Ҷе…°пјҢд»ҘеҸҠеҫҢдҫҶзҡ„жіўзҫҺжӢүе°јдәһпјҲжіўе…°зЁұзӮәжіўиҺ«зҲҫиҢІж јдҪҶж–ҜеҹәпјүгҖҒеә«дәһз¶ӯдәһе’ҢеӨҡеёғеІ‘е…°зҡ„жіўиҳӯеңҹең°гҖӮ йҡЁи‘—з«Ӣйҷ¶е®ӣзҡ„еҹәзқЈж•ҷеҢ–пјҢи©І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зҗҶи«–дёҠеӨұеҺ»дәҶеңЁжӯҗжҙІзҡ„дё»иҰҒзӣ®зҡ„гҖӮ然иҖҢе®ғзҷјиө·дәҶиЁұеӨҡйҮқе°Қе…¶еҹәзқЈж•ҷй„°еңӢжіўиҳӯзҺӢеңӢгҖҒз«Ӣйҷ¶е®ӣеӨ§е…¬еңӢе’Ңи«ҫеӨ«е“Ҙзҫ…еҫ·е…ұе’ҢеңӢзҡ„жҲҳж–—пјҲеңЁеҗёж”¶дәҶ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йЁҺеЈ«еңҳд№ӢеҫҢпјүгҖӮ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ж“Ғжңүеј·еӨ§зҡ„經жҝҹеҹәзӨҺпјҢдҪҝд»–еҖ‘иғҪеӨ еҫһжӯҗжҙІеҗ„ең°еғұеӮӯеғұеӮӯи»ҚдҫҶеўһеҠ д»–еҖ‘зҡ„е°Ғе»әеҫөеҸ¬е…өпјҢд»–еҖ‘д№ҹжҲҗзӮәдәҶжіўзҫ…зҡ„жө·зҡ„йҮҚиҰҒжө·и»ҚеҠӣйҮҸгҖӮ1410е№ҙпјҢдёҖж”Ҝжіўиҳӯ-з«Ӣйҷ¶е®ӣи»ҚйҡҠеңЁеқҰиғҪе ЎжҲ°еҪ№дёӯжұәе®ҡжҖ§ең°ж“Ҡж•—дәҶйЁҺеЈ«еңҳдёҰз ҙеЈһдәҶе…¶и»ҚдәӢеҜҰеҠӣгҖӮ然иҖҢ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йҰ–йғҪеңЁйҡЁеҫҢзҡ„йҰ¬зҲҫе ЎеңҚж”»дёӯиў«жҲҗеҠҹдҝқиЎӣпјҢеӣ иҖҢе…Қж–јеҙ©жҪ°гҖӮ 1515е№ҙпјҢзҘһиҒ–зҫ…йҰ¬еёқеңӢзҡҮеёқйҰ¬е…ӢиҘҝзұіеҲ©е®үдёҖдё–иҲҮжіўиҳӯз«Ӣйҷ¶е®ӣзҡ„йҪҠж ји’ҷзү№дёҖдё–зөҗзӮәиҒҜ姻гҖӮжӯӨеҫҢпјҢеёқеңӢдёҚж”ҜжҢҒеҸҚе°Қжіўиҳӯзҡ„е‘Ҫд»ӨгҖӮ1525е№ҙпјҢеӢғиҳӯзҷ»е Ўзҡ„йҳҝзҲҫеёғйӣ·еёҢзү№з»§д»»еӨ§еӣўй•ҝпјҢеҗҺиҫӯиҒ·дёҰзҡҲдҫқи·Ҝеҫ·ж•ҷпјҢжҲҗзӮәжҷ®йӯҜеЈ«е…¬зҲөпјҢе°Ҷжҷ®йІҒеЈ«дё–дҝ—еҢ–并жҲҗзӮәжіўиҳӯзҡ„йҷ„еәёгҖӮдёҚд№…д№ӢеҫҢйЁҺеЈ«еңҳеӨұеҺ»дәҶ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еҸҠе…¶еңЁеҫ·ж„Ҹеҝ—ж–°ж•ҷең°еҚҖзҡ„иІЎз”ўгҖӮзӣҙеҲ°1809е№ҙжӢҝз ҙеҙҷВ·жіўжӢҝе·ҙдёӢд»Өи§Јж•Ј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еӨұеҺ»дәҶжңҖеҫҢзҡ„дё–дҝ—иІЎз”ў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зўәеҜҰдҝқз•ҷдәҶе…¶еңЁеҫ·ж„Ҹеҝ—еӨ©дё»ж•ҷең°еҚҖзҡ„еӨ§йҮҸиІЎз”ўгҖӮ 然иҖҢйЁҺеЈ«еңҳдҪңзӮәдёҖеҖӢж…Ҳе–„е’Ңе„ҖејҸеңҳй«”з№јзәҢеӯҳеңЁгҖӮе®ғж–ј1938е№ҙиў«зҙҚзІ№еҫ·еңӢеҸ–з· пјҢдҪҶеңЁ1945е№ҙйҮҚж–°е»әз«ӢпјҢжҖ»йғЁи®ҫзҪ®дәҺз»ҙд№ҹзәігҖӮд»ҠеӨ©е®ғдё»иҰҒеңЁдёӯжӯҗй–Ӣеұ•ж…Ҳе–„жҙ»еӢ•гҖӮ йЁҺеЈ«еҖ‘з©ҝи‘—её¶жңүй»‘иүІеҚҒеӯ—жһ¶зҡ„зҷҪиүІеӨ–еҘ—гҖӮеҚҒеӯ—ең–жЎҲжңүжҷӮиў«з”ЁдҪңд»–еҖ‘зҡ„еҫҪз« гҖӮжӯӨең–еғҸеҫҢдҫҶиў«жҷ®йӯҜеЈ«зҺӢеңӢе’Ңеҫ·еңӢз”ЁдҪңи»ҚдәӢиЈқйЈҫе’ҢеҫҪз« пјҢдҫӢеҰӮйҗөеҚҒеӯ—еӢіз« гҖҒеҠҹеӢӢеӢӢз« гҖҒеҫ·еӣҪеӣҪйҳІеҶӣе’ҢзҺ°д»Јеҫ·еӣҪеҶӣйҳҹзҡ„еҫҪз« гҖӮ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еә§еҸійҠҳжҳҜпјҡвҖң幫еҠ©гҖҒдҝқиЎӣгҖҒжІ»ж„ҲвҖқпјҲеҫ·иӘһпјҡHelfen, Wehren, Heilenпјү е»әз«Ӣ 第дёүж¬ЎеҚҒеӯ—еҶӣдёңеҫҒпјҲ1189пјҚ1192е№ҙпјүжңҹй—ҙпјҢеӨ§жү№еҫ·ж„Ҹеҝ—йӘ‘еЈ«еҠ е…ҘдёңеҫҒеҶӣйҳҹпјҢеёҢжңӣйңҚдәЁж–Ҫйҷ¶иҠ¬зҺӢжңқзҡ„и…“зү№зғҲдёҖдё–зҺҮйўҶ他们еҸ–еҫ—иғңеҲ©гҖӮ 然иҖҢи…“зү№зғҲдёҖдё–дёҚе№ёеңЁдёҖжқЎе°ҸжІідёӯжәәдәЎпјҢжҠөиҫҫйҳҝеҚЎзҡ„еҫ·ж„Ҹеҝ—йӘ‘еЈ«зҫӨйҫҷж— йҰ–пјҢйҘұеҸ—й…·зғӯдёҺз–ҫз—…жүҖжү°гҖӮ常规зҡ„еҶӣдәӢеҚ•дҪҚдёҺеҢ»йҷўйӘ‘еЈ«еӣўдёҚе ӘйҮҚиҙҹпјҢжӮЈз—…зҡ„еҫ·ж„Ҹеҝ—дәәеҫҲйҡҫеҫ—еҲ°еҸҠж—¶зҡ„ж•‘жІ»гҖӮ еңЁ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дёҖдәӣжқҘиҮӘдёҚжқҘжў…е’Ңеҗ•иҙқе…Ӣзҡ„еҚҒеӯ—еҶӣеҶіе®ҡз»„е»әеҫ·ж„Ҹеҝ—дәәзҡ„еҢ»йҷўдҝ®дјҡпјҢеҚівҖң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ңЈзҺӣеҲ©дәҡеҢ»йҷўеҫ·ж„Ҹеҝ—е…„ејҹйӘ‘еЈ«еӣўвҖқпјҲжӢүдёҒиӘһпјҡOrdo domus Sanctae Mariae Theutonicorum IerosolimitanorumпјүгҖӮ[7]1197е№ҙпјҢдҝ®дјҡжҲҗе‘ҳеҶіе®ҡдёәдёҖдәӣеүҚзәҝеҹҺе ЎжҸҗдҫӣй©»йҳІпјҢеӣ жӯӨ他们иҜ·жұӮж•ҷе®—еЎһиҺұж–Ҝе»·дёүдё–жү№еҮҶ他们жҲҗдёәеҶӣдәӢдҝ®дјҡзҡ„иҜ·жұӮгҖӮ第дәҢе№ҙпјҢж•ҷе®—йўҒеҸ‘дәҶж–°зҡ„зү№и®ёзҠ¶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ҫ—д»ҘжҲҗз«ӢпјҢйҳҝеҚЎжҲҗдёәйӘ‘еЈ«еӣўжҖ»йғЁпјҢзӣҙиҮі1291е№ҙиў«ж”»еҚ гҖӮ 1199е№ҙ9жңҲ19ж—ҘпјҢж•ҷе®—дҫқиҜәеўһзҲөдёүдё–йўҒеёғи®ӯд»ӨпјҢ规е®ҡ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жҠ«е’ҢеңЈж®ҝйӘ‘еЈ«дёҖж ·зҡ„жҠ«йЈҺпјҲзҷҪиүІжҠ«йЈҺпјҢеҲәз№Ўзҡ„зҙӢз« з”ұиҒ–ж®ҝ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зҙ…еҚҒеӯ—ж”№зӮә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иұЎеҫөй»‘еҚҒеӯ—пјүпјҢдёҰжү§иЎҢе’ҢеҢ»йҷўйӘ‘еЈ«еӣўдёҖж ·зҡ„еӣўи§„гҖӮ 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жңҖеҲқзҡ„еҠҝеҠӣеҫҲе°ҸпјҢ他们зҡ„йўҶең°дёҺеҹҺе ЎеӨ§еӨҡжқҘиҮӘе…¶д»–йўҶдё»зҡ„йҰҲиө гҖӮ1195е№ҙ4жңҲпјҢйҰҷж§ҹеҢәзҡ„дәЁеҲ©дјҜзҲөиө жҸҗе°”пјҲд»Ҡй»Һе·ҙе«©еўғеҶ…пјүдҪңдёәжҚ®зӮ№пјҢ1196е№ҙ3жңҲеҶҚиө е…¶еңЁйӣ…жі•пјҲд»Ҡзү№жӢүз»ҙеӨ«йҷ„иҝ‘пјүзҡ„е°ҒйӮ‘пјӣеҸҰжңүзҘһиҒ–зҫ…йҰ¬еёқеңӢзҡҮеёқдәЁеҲ©е…ӯдё–еңЁ1197е№ҙиө йҖҒж„ҸеӨ§еҲ©е’ҢиҘҝиҘҝйҮҢзҡ„ж•ҷе ӮгҖҒдҝ®йҒ“йҷўе’ҢеҢ»йҷўпјҢйҖҗжёҗеңЁ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ң°еҢәеҪўжҲҗеҠҝеҠӣгҖӮ еҸ‘еұ•ең°дёӯжө·зҡ„еӣ°еўғ13дё–зәӘеҲқпјҢйҡҸзқҖеҢ»йҷўйӘ‘еЈ«еӣўе’ҢеңЈж®ҝйӘ‘еЈ«еӣўеҜ№з«ӢеҠ еү§пјҢеҢ»йҷўйӘ‘еЈ«еӣўжӢүжӢў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д»ҘеҜ№жҠ—жҺ§еҲ¶зқҖ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ң°еҢәдё»иҰҒеҶӣдәӢжҚ®зӮ№зҡ„еңЈж®ҝйӘ‘еЈ«еӣўпјҢе…¶й—ҙ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д»ҺеҢ»йҷўйӘ‘еЈ«еӣўжүӢдёӯиҺ·иҙҲ马еҠ зү№е ЎгҖӮ 1210е№ҙпјҢиө«е°”жӣјВ·еҶҜВ·иҗЁе°”жүҺпјҲc.1165-1239пјүжӢ…д»»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ӣўй•ҝ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е…¶жҢҮжҢҘдёӢеңЁ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ң°еҢәиҺ·еҫ—дёҖе®ҡзҡ„иғңеҲ©пјҢ并еҸӮдёҺ第дә”ж¬ЎеҚҒеӯ—еҶӣдёңеҫҒпјҢиҝӣе…ҘеҹғеҸҠпјҢдҪҶжңҖеҗҺеңЁжӣјиӢҸжӢүжҲҳеҪ№пјҲ1221е№ҙ8жңҲ30ж—ҘпјүдёӯжғЁиҙҘпјҢиө«зҲҫжӣјВ·йҰ®В·иҗЁзҲҫжүҺдёҺеңЈж®ҝйӘ‘еЈ«еӣўеӣўй•ҝдёҖеҗҢиў«дҝҳгҖӮеңЁиө«зҲҫжӣјВ·йҰ®В·иҗЁзҲҫжүҺжӢ…д»»еӣўй•ҝжңҹй—ҙ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иҺ·еҫ—ж•ҷе»·йўҒеҸ‘зҡ„иөҺзҪӘиҜҒпјҲ1216е№ҙ2жңҲ18ж—ҘпјүпјҢд»ҘеҸҠж•ҷе®—дҪ•и«ҫдёүдё–жҺҲдәҲзҡ„113йЎ№зү№жқғпјҲ1221е№ҙ1жңҲ9ж—ҘпјүгҖӮ еңЁеҢҲзүҷеҲ©зҡ„е°қиҜ• 1211е№ҙпјҢеҢҲзүҷеҲ©зҡ„е®үеҫ·зғҲдәҢдё–йӮҖиҜ·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үҚеҫҖзү№е…°иҘҝз“Ұе°јдәҡеё®еҠ©йҒҸеҲ¶еә“жӣјдәәзҡ„жү©еј пјҢеҘҪи®©д»–еҸҜд»Ҙдё“еҝғеҸӮеҠ еҚҒеӯ—еҶӣдёңеҫҒгҖӮе®үеҫ·зғҲдәҢдё–жүҝиҜәйӘ‘еЈ«еӣўеҸҜд»ҘеңЁзү№е…°иҘҝз“Ұе°јдәҡзҡ„еёғеІ‘е…°пјҲBurzenlandпјүе®ҡеұ…пјҢ并且е…ҚйҷӨдәҶйӘ‘еЈ«еӣўи®ёеӨҡзЁҺзӣ®гҖӮйӘ‘еЈ«еӣўеҜ№иҝҷйЎ№ж–°дҪҝе‘ҪиЎЁзҺ°еҮәдәҶжһҒеӨ§зғӯжғ…пјҢеҲ°1220е№ҙ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·Із»ҸеңЁиҝҷзүҮеңҹең°дёҠе»әз«ӢдәҶ5еә§еҹҺе ЎпјҢ并且жӢ’з»қдёҺеҪ“ең°зҡ„иҙөж—ҸеҲҶдә«иғңеҲ©жһңе®һпјҢиҝҷеј•иө·дәҶеҢҲзүҷеҲ©иҙөж—Ҹе’Ңж•ҷ士们зҡ„дёҚж»ЎдёҺзҢңеҝҢгҖӮ дёәдәҶдҝқжҠӨ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ж—ўеҫ—еҲ©зӣҠпјҢеӨ§еӣўй•ҝиө«зҲҫжӣјВ·йҰ®В·иҗЁзҲҫжүҺеҗ‘ж•ҷе®—жҸҗеҮәиҜ·жұӮпјҢе°Ҷ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ңҹең°зҪ®дәҺж•ҷе»·дҝқжҠӨд№ӢдёӢпјҢзү№е…°иҘҝз“Ұе°јдәҡ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е®һйҷ…дёҠжҲҗдёәдәҶж•ҷе»·зҡ„йҮҮйӮ‘пјҢеҺҹе…Ҳж”ҜжҢҒ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ҢҲзүҷеҲ©еӣҪзҺӢд№ҹиў«жҝҖжҖ’пјҢдёӢд»Өе°ҶйӘ‘еЈ«еӣўй©ұйҖҗеҮәеўғгҖӮ иҮіжӯӨ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еҢҲзүҷеҲ©зҡ„е°қиҜ•д»ҘжғЁиҙҘе‘Ҡз»ҲгҖӮ[7]  иҝӣеҶӣжҷ®йІҒеЈ« еңЁ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Ұ»ејҖеҢҲзүҷеҲ©еҗҺпјҢеҢҲзүҷеҲ©дёҚеҫ—дёҚиҮӘе·ұеҜ№жҠ—дёңж–№жёёзү§ж°‘ж—Ҹзҡ„еЁҒиғҒгҖӮ1241е№ҙпјҢйһ‘йқјдәәеӨ§дёҫе…Ҙдҫөдёң欧пјҢдёҖи·Ҝжү“иҮіеҢҲзүҷеҲ©е№¶е°Ҷж—¶д»»еҢҲзүҷеҲ©еӣҪзҺӢиҙқжӢүеӣӣдё–й©ұйҖҗиҮіеҘҘең°еҲ©еӨ§е…¬еӣҪгҖӮеҢҲзүҷеҲ©еҢ—йғЁзҡ„жіўе…°зҺӢеӣҪд№ҹжҚҹеӨұжғЁйҮҚпјҢж— еҠӣйҳІеҫЎжёёзү§ж°‘ж—Ҹзҡ„дҫөз•ҘгҖӮ 1226е№ҙпјҢжіўе…°дёңеҢ—йғЁзҡ„马дҪҗеӨ«иҲҚе…¬зҲөеә·жӢүеҫ·дёҖдё–иҜ·жұӮйӘ‘еЈ«еӣўеё®еҠ©дҝқеҚ«д»–зҡ„иҫ№еўғ并еҫҒи®ЁжіўзҪ—зҡ„жө·жҷ®йІҒеЈ«ең°еҢәзҡ„еҺҹдҪҸж°‘пјҲеҸӨжҷ®йІҒеЈ«дәәпјүпјҢ并е…Ғи®ёйӘ‘еЈ«еӣўй©»жүҺеңЁеә«зҲҫй»ҳиҳӯпјҢиҝҷдёҖдәӢ件д№ҹиў«и®ӨдёәжҳҜвҖңеҢ—ж–№еҚҒеӯ—еҶӣдёңеҫҒвҖқ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гҖӮ1226е№ҙ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дёҺзҘһиҒ–зҫ…йҰ¬еёқеңӢзҡҮеёқи…“зү№зғҲдәҢдё–иҫҫжҲҗеҚҸи®®пјҢиҺ·еҫ—жҷ®йІҒеЈ«еўғеҶ…зҡ„жүҖжңүиҙөж—Ҹзү№жқғгҖӮ1234е№ҙ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иөўеҫ—з‘ҹж јзәіжҲҳеҪ№зҡ„иғңеҲ©пјҢж•ҷе»·жҺ§еҲ¶жҷ®йІҒеЈ«е…ЁеўғпјҢе°Ҷд№Ӣз§ҹеҖҹз»ҷ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пјҢдҪҶзӣҙеҲ°1285е№ҙ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жүҚжңҖз»ҲеҫҒжңҚжҷ®йІҒеЈ«пјҢиҝ«дҪҝжҷ®йІҒеЈ«дәәж”№е®—еӨ©дё»ж•ҷгҖӮ зӮәдәҶеҪҢиЈңзҳҹз–«йҖ жҲҗзҡ„жҗҚеӨұдёҰеҸ–д»ЈйғЁеҲҶж»…зө•зҡ„еңҹи‘—дәәеҸЈ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йј“еӢөдҫҶиҮӘзҘһиҒ–зҫ…йҰ¬еёқеңӢпјҲдё»иҰҒжҳҜеҫ·ж„Ҹеҝ—дәәгҖҒдҪӣиҳӯиҠ’дәәе’ҢиҚ·иҳӯдәәпјүе’ҢеҫҢдҫҶзҡ„йҰ¬зҘ–йҮҢдәәйҰ¬зҙўз¶ӯдәһпјҲжіўиҳӯдәәпјүзҡ„移民гҖӮ йҖҷдәӣдәәеҢ…жӢ¬иІҙж—ҸгҖҒеёӮж°‘е’ҢиҫІж°‘пјҢеҖ–еӯҳзҡ„иҖҒжҷ®йӯҜеЈ«дәәйҖҡйҒҺж—ҘиҖіжӣјеҢ–йҖҗжјёеҗҢеҢ–гҖӮ е®ҡеұ…иҖ…еңЁеүҚжҷ®йӯҜеЈ«е®ҡеұ…й»һдёҠе»әз«ӢдәҶиЁұеӨҡеҹҺйҺ®гҖӮ йЁҺеЈ«еңҳиҮӘе·ұе»әйҖ дәҶиЁұеӨҡеҹҺе ЎпјҲеҘ§зҷ»ж–Ҝе ЎпјүпјҢеңЁйӮЈиЈЎе®ғеҸҜд»Ҙж“Ҡж•—еҸӨжҷ®йӯҜеЈ«дәәзҡ„иө·зҫ©пјҢдёҰз№јзәҢж”»ж“Ҡз«Ӣйҷ¶е®ӣеӨ§е…¬еңӢе’ҢжіўиҳӯзҺӢеңӢпјҢеңЁ14дё–зҙҖпјҢйЁҺеЈ«еңҳ經常иҲҮд№ӢдәӨжҲ° е’Ң15дё–зҙҖгҖӮ йЁҺеЈ«еңҳе»әз«Ӣзҡ„дё»иҰҒеҹҺйҺ®еҢ…жӢ¬иүҫеҖ«ж–Ҫжі°еӣ (Olsztyn)гҖҒеҹғзҲҫиі“ (ElblД…g)гҖҒжў…жў…е°” (Memel) е’ҢжҹҜе°јж–Ҝе Ў (KГ¶nigsberg)пјҢйҖҷдәӣеҹҺйҺ®е»әж–ј 1255 е№ҙпјҢжҳҜзӮәдәҶзҙҖеҝөжіўеёҢзұідәһеңӢзҺӢеҘ§жүҳеҚЎдәҢдё– (Otakar II)пјҢдҪҚж–јиў«жҜҖзҡ„жҷ®йӯҜеЈ«е®ҡеұ…й»һзҡ„йҒәеқҖдёҠгҖӮ еҙӣиө·еҲ©жІғе°јдәҡ 1237е№ҙ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еңЁзҙўеӢ’жҲ°еҪ№дёӯж…ҳж•—еҫҢпјҢ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еҜ¶еҠҚе…„ејҹеңҳиў«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еҗёж”¶гҖӮ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еҲҶж”ҜйҡЁеҫҢиў«зЁұзӮә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йЁҺеЈ«еңҳгҖӮ當йЁҺеЈ«еңЁ1242е№ҙзҡ„еҶ°жІід№ӢжҲ°дёӯж…ҳж•—ж–ји«ҫеӨ«е“Ҙзҫ…еҫ·зҡ„дәһжӯ·еұұеӨ§В·ж¶…еӨ«ж–ҜеҹәдәІзҺӢжүӢдёӯжҷӮпјҢи©Ұең–еҗ‘зҫ…ж–Ҝж“ҙејөзҡ„еҳ—и©ҰеӨұж•—дәҶгҖӮеңЁжҺҘдёӢдҫҶзҡ„е№ҫеҚҒе№ҙиЈЎ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е°ҲжіЁж–јеҫҒжңҚеә«зҲҫж–Ҝдәәе’Ңз‘ҹзұіеҲ©дәһдәәгҖӮ1260е№ҙпјҢе®ғеңЁжқңзҲҫиІқжҲ°еҪ№дёӯиҲҮи–©иҺ«еҗүжҸҗдәһдәәж…ҳж•—пјҢеј•зҷјдәҶжҷ®йӯҜеЈ«е’Ң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еҗ„ең°зҡ„еҸӣдәӮгҖӮ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еңЁ1262е№ҙиҮі1265е№ҙзҡ„жҹҜе°јж–Ҝе ЎеңҚеҹҺжҲ°дёӯеҸ–еҫ—й—ңйҚөеӢқеҲ©еҫҢпјҢжҲ°зҲӯйҒ”еҲ°дәҶиҪүжҠҳй»һгҖӮеә«зҲҫж–ҜдәәжңҖзөӮеңЁ1267е№ҙиў«еҫҒжңҚпјҢиҖҢеЎһзұіеҲ©дәһдәәеүҮеңЁ1290е№ҙиў«еҫҒжңҚгҖӮйЁҺеЈ«еңҳеңЁ1343е№ҙиҮі1345е№ҙйҺ®еЈ“дәҶдёҖж¬ЎйҮҚеӨ§зҡ„ж„ӣжІҷе°јдәһеҸӣдәӮпјҢдёҰж–ј1346е№ҙеҫһдё№йәҘжүӢдёӯиіјиІ·дәҶж„ӣжІҷе°јдәһе…¬еңӢгҖӮ з«Ӣйҷ¶е®ӣеңЁ14дё–зҙҖеҲқпјҢй—ңж–јжіўжў…йҮҢеҲ©дәһе…¬еңӢз№јжүҝж¬Ҡзҡ„зҲӯз«ҜдҪҝйЁҺеЈ«еңҳжҚІе…ҘдәҶйҖІдёҖжӯҘзҡ„иЎқзӘҒгҖӮ1306е№ҙпјҢжіўиҳӯеңӢзҺӢжә«еЎһж–ҜеӢһж–ҜеҺ»дё–еҫҢпјҢеӢғиҳӯзҷ»е ЎдҫҜзҲөе°Қе…¬еңӢжҸҗеҮәдәҶиҰҒжұӮгҖӮжіўиҳӯзҡ„иӮҳй«ҳеӨ§е…¬з“ҰиҝӘж–Ҝз“ҰеӨ«дёҖдё–д№ҹж №ж“ҡжҷ®зҶұжў…ж–Ҝз“ҰеӨ«дәҢдё–зҡ„з№јжүҝж¬ҠиҰҒжұӮе…¬еңӢпјҢдҪҶйҒӯеҲ°еҸҚе°ҚдёҖдәӣжіўзҫҺжӢүе°јдәһиІҙж—ҸгҖӮд»–еҖ‘еҗ‘еӢғиҳӯзҷ»е Ўи«ӢжұӮ幫еҠ©пјҢеӢғиҳӯзҷ»е ЎйҡЁеҫҢеңЁ1308е№ҙдҪ”й ҳдәҶйҷӨж јдҪҶж–Ҝе…ӢеҹҺе ЎеӨ–зҡ„ж•ҙеҖӢжіўзҫҺз‘һеҲ©дәһгҖӮз”ұж–јз“ҰиҝӘж–Ҝз“ҰеӨ«з„Ўжі•дҝқиЎӣж јдҪҶж–Ҝе…ӢпјҢ當жҷӮз”ұеӨ§еӣўй•ҝйҪҠж јеј—йҮҢеҫ·В·йҰ®В·иІ»еёҢзү№ж—әж №зҺҮй ҳзҡ„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иў«иҰҒжұӮй©…йҖҗеӢғиҳӯзҷ»е ЎдәәгҖӮ еҜ№жҠ—жіўе…° 1308е№ҙ9жңҲпјҢжҷ®йӯҜеЈ«йўҶдё»жө·еӣ йҮҢеёҢВ·йҰ®В·жҷ®жҙӣиҢЁе…Ӣ(Heinrich von PlГ¶tzke)й ҳе°Һзҡ„йЁҺеЈ«еңҳе°ҮеӢғиҳӯзҷ»е ЎдәәйҖҗеҮәж јдҪҶж–Ҝе…ӢпјҢдҪҶйҡЁеҫҢжӢ’зө•е°Үи©ІйҺ®и®“зөҰжіўиҳӯдәәпјҢж“ҡдёҖдәӣж¶ҲжҒҜдҫҶжәҗзЁұпјҢи©ІйҺ®зҡ„еұ…ж°‘йҒӯеҲ°еұ ж®әгҖӮе„ҳз®ЎжҡҙеҠӣзҡ„зўәеҲҮзЁӢеәҰе°ҡдёҚжё…жҘҡпјҢдҪҶжӯ·еҸІеӯёе®¶жҷ®йҒҚиӘҚзӮәйҖҷжҳҜдёҖеҖӢз„Ўжі•и§Јй–Ӣзҡ„и¬ҺеңҳгҖӮдј°иЁҲзҜ„еңҚеҫһи©Іең°еҚҖзҡ„ж”ҝиҰҒе’ҢйЁҺеЈ«з·Ёе№ҙеҸІе®¶е ұе‘Ҡзҡ„60еҗҚеҸӣдәӮй ҳе°ҺдәәеҲ°10,000еҗҚе№іж°‘пјҢйҖҷдёҖж•ёеӯ—еңЁж•ҷзҡҮи©”жӣёдёӯиў«еј•з”ЁпјҢз”Ёж–јжҮІзҪ°и©ІдәӢ件зҡ„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жі•еҫӢзЁӢеәҸпјӣжі•еҫӢзіҫзҙӣжҢҒзәҢдәҶдёҖж®өжҷӮй–“пјҢдҪҶе‘Ҫд»ӨжңҖзөӮиў«е…ҚйҷӨдәҶжҢҮжҺ§гҖӮеңЁзҙўзҲҫдёҒжўқзҙ„дёӯпјҢ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ж–ј1309е№ҙ9жңҲ13ж—Ҙд»Ҙ10,000йҰ¬е…Ӣзҡ„еғ№ж јеҫһдҫҜзҲөжүӢдёӯиіјиІ·дәҶеӢғиҳӯзҷ»е Ўе°Қж јдҪҶж–Ҝе…ӢгҖҒеёҢз¶ӯеҲҮе’Ңзү№еҲҮеӨ«еҹҺе ЎеҸҠе…¶и…№ең°зҡ„жүҖи¬Ӯе®ЈзЁұгҖӮ  е°ҚжіўзҫҺз‘һеҲ©дәһзҡ„жҺ§еҲ¶дҪҝйЁҺеЈ«еңҳиғҪеӨ е°Үд»–еҖ‘зҡ„дҝ®йҒ“йҷўеңӢ家иҲҮзҘһиҒ–зҫ…йҰ¬еёқеңӢзҡ„йӮҠз•ҢйҖЈжҺҘиө·дҫҶгҖӮеҚҒеӯ—и»Қзҡ„еўһжҸҙе’ҢиЈңзөҰеҸҜд»ҘеҫһеёқеңӢй ҳеңҹиҘҝжіўзҫҺжӢүе°јдәҡйҖҡйҒҺжіўзҫҺз‘һеҲ©дәһеҲ°йҒ”жҷ®йӯҜеЈ«пјҢиҖҢжіўиҳӯйҖҡеҫҖжіўзҫ…зҡ„жө·зҡ„йҖҡйҒ“иў«е°ҒйҺ–гҖӮйӣ–然波иҳӯдё»иҰҒжҳҜйЁҺеЈ«зҡ„зӣҹеҸӢпјҢеҸҚе°Қз•°ж•ҷзҡ„жҷ®йӯҜеЈ«дәәе’Ңз«Ӣйҷ¶е®ӣдәәпјҢдҪҶе°ҚжіўзҫҺз‘һеҲ©дәһзҡ„дҪ”й ҳдҪҝйҖҷеҖӢзҺӢеңӢи®ҠжҲҗдәҶ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е …е®ҡж•өдәәгҖӮ ж јдҪҶж–Ҝе…Ӣзҡ„дҪ”й ҳжЁҷиӘҢи‘—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жӯ·еҸІзҡ„дёҖеҖӢж–°йҡҺж®өгҖӮ1307е№ҙй–Ӣе§Ӣзҡ„е°Қеј·еӨ§зҡ„иҒ–ж®ҝ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иҝ«е®іе’Ңе»ўйҷӨд»Ө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ж„ҹеҲ°ж“”жҶӮпјҢдҪҶе°ҚжіўиҺ«з‘һеҲ©дәһзҡ„жҺ§еҲ¶дҪҝд»–еҖ‘иғҪеӨ еңЁ1309е№ҙе°ҮзёҪйғЁеҫһеЁҒе°јж–Ҝжҗ¬еҲ°и«ҫеҠ зү№жІідёҠзҡ„йҰ¬зҲҫе ЎпјҢдё–дҝ—ж¬ҠеҠӣз„Ўжі•и§ёеҸҠ.жҷ®йӯҜеЈ«иҳӯеҫ·жў…ж–Ҝзү№зҡ„иҒ·дҪҚиҲҮеӨ§еӣўй•ҝзҡ„иҒ·дҪҚеҗҲдҪөгҖӮж•ҷзҡҮй–Ӣе§ӢиӘҝжҹҘйЁҺеЈ«зҡ„дёҚ當иЎҢзӮәпјҢдҪҶжІ’жңүзҷјзҸҫд»»дҪ•жҢҮжҺ§жңүеҜҰиіӘе…§е®№гҖӮйҡЁи‘—еҸҚе°Қз«Ӣйҷ¶е®ӣдәәзҡ„йҒӢеӢ•пјҢйЁҺеЈ«еҖ‘йқўиҮЁи‘—е ұеҫ©жҖ§зҡ„жіўиҳӯе’ҢдҫҶиҮӘж•ҷзҡҮзҡ„жі•еҫӢеЁҒи„…гҖӮ 1343е№ҙзҡ„еҚЎеҲ©иҢІжўқзҙ„зөҗжқҹдәҶ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иҲҮжіўиҳӯд№Ӣй–“зҡ„е…¬й–ӢжҲ°зҲӯгҖӮйЁҺеЈ«еңҳе°Үеә«дәһз¶ӯдәһе’ҢеӨҡеёғжҙҘеңҹең°и®“зөҰжіўиҳӯпјҢдҪҶе°Үжө·зғҸе§Ҷи«ҫеңҹең°е’Ңжіўжў…йӣ·еҲ©дәһиҲҮж јдҪҶж–Ҝе…ӢпјҲж—ҘиҖіжӣјеҢ–зӮәдҪҶжҫӨпјҲDanzigпјүпјүдҝқз•ҷдәҶдёӢдҫҶгҖӮ еҠҝеҠӣзҡ„е·…еі° 1337е№ҙпјҢзҡҮеёқи·Ҝжҳ“еӣӣдё–жҺҲдәҲйЁҺеЈ«еңҳеҫҒжңҚжүҖжңүз«Ӣйҷ¶е®ӣе’Ңдҝ„зҫ…ж–Ҝзҡ„еёқеңӢзү№ж¬ҠгҖӮеңЁеӨ§еӣўй•ҝжә«йҮҢеёҢВ·йҰ®В·е…Ӣе°јжҷ®зҫ…еҫ·пјҲ1351-1382е№ҙпјүзөұжІ»жңҹй–“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еңӢйҡӣиҒІжңӣйҒ”еҲ°й Ӯеі°пјҢдёҰжҺҘеҫ…дәҶзңҫеӨҡжӯҗжҙІеҚҒеӯ—и»Қе’ҢиІҙж—ҸгҖӮ з‘һе…ёеңӢзҺӢйҳҝзҲҫдјҜзү№е°Үе“Ҙзү№иҳӯеі¶еүІи®“зөҰйЁҺеЈ«еңҳдҪңзӮәдҝқиӯүпјҲйЎһдјјж–је°Ғең°пјүпјҢдёҰзҗҶи§Јд»–еҖ‘е°Үеҫһжіўзҫ…зҡ„жө·йҖҷеҖӢжҲ°з•Ҙеі¶е¶јеҹәең°ж¶Ҳж»…жө·зӣңжө·зӣңгҖӮ1398е№ҙпјҢеӨ§еңҳй•·еә·жӢүеҫ·В·йҰ®В·е®№йҮ‘ж №зҺҮй ҳзҡ„дёҖж”Ҝе…ҘдҫөйғЁйҡҠеҫҒжңҚдәҶи©Іеі¶пјҢдёҰе°ҮVictualе…„ејҹ趕еҮәдәҶе“Ҙзү№иҳӯеі¶е’Ңжіўзҫ…зҡ„жө·гҖӮ 1386е№ҙпјҢз«Ӣйҷ¶е®ӣеӨ§е…¬йӣ…и“ӢжІғжҺҘеҸ—еҹәзқЈж•ҷжҙ—зҰ®пјҢиҲҮжіўиҳӯзҺӢеҗҺйӣ…еҫ·з¶ӯеҠ зөҗе©ҡпјҢеҸ–еҗҚзӮәз“ҰиҝӘж–Ҝз“ҰеӨ«дәҢдё–йӣ…и“ӢжІғпјҢжҲҗзӮәжіўиҳӯеңӢзҺӢгҖӮйҖҷеңЁе…©еңӢд№Ӣй–“е»әз«ӢдәҶеҖӢдәәиҒҜзӣҹпјҢдёҰжҲҗзӮә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жҪӣеңЁеј·еӨ§е°ҚжүӢгҖӮйЁҺеЈ«еңҳжңҖеҲқиЁӯжі•и®“з“ҰиҝӘж–Ҝз“ҰеӨ«дәҢдё–В·йӣ…и“ӢжІғе’Ңд»–зҡ„е Ӯе…„з¶ӯйҷ¶еЎ”ж–Ҝзӣёдә’е°ҚжҠ—пјҢдҪҶ當з¶ӯйҷ¶еЎ”ж–Ҝй–Ӣе§ӢжҮ·з–‘йЁҺеЈ«еңҳиЁҲеҠғеҗһдҪөд»–зҡ„йғЁеҲҶй ҳеңҹжҷӮпјҢйҖҷдёҖзӯ–з•ҘеӨұж•—дәҶгҖӮ йӣ…и“ӢжІғзҡ„жҙ—зҰ®й–Ӣе§ӢдәҶз«Ӣйҷ¶е®ӣжӯЈејҸзҡҲдҫқеҹәзқЈж•ҷзҡ„йҒҺзЁӢгҖӮе„ҳз®ЎеңЁжҷ®йӯҜеЈ«е’Ңз«Ӣйҷ¶е®ӣжӯЈејҸжҲҗзӮәеҹәзқЈж•ҷеҫ’еҫҢ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жҲҗз«Ӣзҡ„зҗҶз”ұе°ұзөҗжқҹдәҶпјҢдҪҶйЁҺеЈ«еңҳиҲҮз«Ӣйҷ¶е®ӣе’Ңжіўиҳӯзҡ„зҲӯеҹ·е’ҢжҲ°зҲӯд»ҚеңЁз№јзәҢгҖӮиңҘиңҙиҒҜзӣҹж–ј1397е№ҙз”ұжҷ®йӯҜеЈ«иІҙж—ҸеңЁеә«зҲҫе§Ҷеүөе»әпјҢд»ҘеҸҚе°Қ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ж”ҝзӯ–гҖӮ 1407е№ҙпјҢ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йҒ”еҲ°дәҶе…¶жңҖеӨ§зҡ„й ҳеңҹзҜ„еңҚпјҢеҢ…жӢ¬жҷ®йӯҜеЈ«гҖҒжіўзҫҺжӢүе°јдәһгҖҒи–©иҺ«еҗүеёҢдәһгҖҒеә«зҲҫиҳӯгҖҒ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гҖҒж„ӣжІҷе°јдәһгҖҒе“Ҙзү№иҳӯгҖҒйҒ”жҲҲгҖҒеҺ„еЎһзҲҫе’ҢиҜәдјҠйҰ¬е…Ӣзҡ„еңҹең°пјҢйҖҷдәӣеңҹең°з”ұеӢғиҳӯзҷ»е ЎеңЁ1402е№ҙ典當гҖӮ иЎ°иҗҪеҶ°ж№–д№ӢжҲҳ1242е№ҙ4жңҲ5ж—ҘпјҢ1дёҮ2еҚғеҗҚеҚҒеӯ—и»Қе’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йғЁйҳҹпјҲеҢ…жӢ¬дё№йәҰе’ҢжіўзҪ—зҡ„жө·жІҝеІёеҗ„ең°зҡ„йӘ‘еЈ«е’Ңж°‘е…өпјүдёҺдәҡеҺҶеұұеӨ§В·ж¶…еӨ«ж–ҜеҹәжҢҮжҢҘзҡ„1дёҮ5еҚғиҮі1дёҮ7еҚғдәәзҡ„иҜәеӨ«е“ҘзҪ—еҫ·е…¬еңӢи»Қйҳҹеұ•ејҖжҘҡеҫ·ж№–жҲҳеҪ№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д»ҘйҮҚйӘ‘е…өдҪңдёәеүҚй”Ӣе’ҢдҪңжҲҳдё»еҠӣпјҢе…¶еҗҺжҳҜжӯҘе…өпјҢдёӨзҝје’ҢеҗҺж–№жңүйҮҚиЈқйЁҺе…өпјҢдҝ„еҶӣеҲҷд»Ҙиј•йӘ‘е…өе’ҢиЈ…еӨҮеј“з®ӯгҖҒжЁҷж§Қзҡ„иҪ»жӯҘе…өй…ҚзҪ®еңЁдёӯеӨ®пјҢиҜәеӨ«е“ҘзҪ—еҫ·е…¬еңӢзҡ„зІҫй”җйҮҚиЈқжӯҘе…өеңЁдёӨзҝјпјҢдәҡеҺҶеұұеӨ§В·ж¶…еӨ«ж–Ҝеҹәзҡ„дәІеҚ«йҳҹе’Ңиҙөж—ҸйӘ‘е…өйҳҹдҪңдёәйў„еӨҮйҳҹеҹӢдјҸеңЁе·ҰзҝјеҗҺдҫ§гҖӮжңҖз»Ҳ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йҮҚиЈқйӘ‘е…өз”ұдәҺиЎҢеҠЁдёҚдҫҝд»ҘеҸҠеҶ°еұӮејҖиЈӮзӯүеҺҹеӣ йҒӯеҲ°жғЁиҙҘпјҢжҚҹеӨұи¶…иҝҮ1дёҮдәәпјҢеҶҚж— иғҪеҠӣеҗ‘дҝ„еӣҪи…№ең°иҝӣеҶӣгҖӮжҘҡеҫ·ж№–жҲҳеҪ№д№ҹиў«з§°дҪңеҶ°ж№–еӨ§жҲҳгҖӮ 1291е№ҙ5жңҲ18ж—ҘпјҢ马з©ҶйІҒе…ӢиӢҸдё№еӣҪйӘ‘е…өж”»йҷ·йҳҝеҚЎпјҢеӨ§еӣўй•ҝеә·жӢүеҫ·В·йҰ®В·иІ»еёҢзү№ж—әж №зҺҮйўҶ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жҖ»йғЁиҝҒеҫҖеЁҒе°јж–ҜгҖӮ1320е№ҙ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ӣўй•ҝеңЁеёҢи…ҠеҚ—йғЁж‘©йҮҢдәҡеҚҠеІӣиў«еҪ“ең°дәәжқҖжӯ»гҖӮ 1346е№ҙ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д»Һдё№йәҰдәәжүӢдёӯеӨәеҸ–зҲұжІҷе°јдәҡпјҢжҺ§еҲ¶дәҶжіўзҪ—зҡ„жө·дёңеІёзҡ„е…ЁйғЁеҮәжө·еҸЈгҖӮ 第дёҖж¬ЎеқҰиғҪе ЎжҲҳеҪ№ 1410е№ҙ7жңҲ15ж—Ҙ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дёҺжіўе…°гҖҒз«Ӣйҷ¶е®ӣгҖҒдҝ„зҪ—ж–ҜиҒ”еҶӣеұ•ејҖж јжһ—з“Ұе°”еҫ·жҲҳеҪ№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иҙҘеҢ—пјҢеҢ…жӢ¬еӨ§еӣўй•ҝд№Ңе°”йҮҢеёҢВ·еҶҜВ·е®№е®Ғж №еңЁеҶ…зҡ„е…ЁйғЁй«ҳзә§жҢҮжҢҘе®ҳйҳөдәЎгҖӮ1440е№ҙпјҢжҷ®йІҒеЈ«ең°еҢәзҡ„д№Ўз»…е’ҢеёӮж°‘е»әз«Ӣжҷ®йӯҜеЈ«йӮҰиҒҜпјҢ1454е№ҙпјҢе®ғиө·дҫҶеҸҚе°ҚйЁҺеЈ«еңҳпјҢиҰҒжұӮжіўиҳӯеңӢзҺӢеҚЎйҪҠзұіж—Ҙеӣӣдё–е°Үи©Іең°еҚҖдҪөе…ҘжіўиҳӯзҺӢеңӢпјҢеңӢзҺӢеҗҢж„ҸдёҰеңЁе…ӢжӢү科еӨ«з°ҪзҪІдәҶдёҖй …еҗҲдҪөжі•жЎҲгҖӮ1454е№ҙ3жңҲеңЁе…ӢжӢү科еӨ«жҲҗз«ӢжҷӮпјҢи©Іең°еҚҖзҡ„еёӮй•·гҖҒеёӮж°‘е’Ңд»ЈиЎЁе®ЈиӘ“ж•Ҳеҝ жіўиҳӯеңӢзҺӢгҖӮйҖҷжЁҷиӘҢи‘—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е’Ңжіўиҳӯд№Ӣй–“зҡ„еҚҒдёүе№ҙжҲ°зҲӯзҡ„й–Ӣе§ӢгҖӮеҚЎиҘҝзұізҲҫеӣӣдё–жҺҲж¬ҠеҗҲдҪөй ҳеңҹзҡ„дё»иҰҒеҹҺеёӮй‘„йҖ жіўиҳӯзЎ¬е№ЈгҖӮжҷ®йӯҜеЈ«зҡ„еӨ§йғЁеҲҶең°еҚҖеңЁжҲ°зҲӯдёӯйҒӯеҲ°з ҙеЈһпјҢеңЁжӯӨжңҹй–“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ж–ј1455е№ҙе°ҮиҜәдјҠйҰ¬е…ӢйҖҒеӣһеӢғиҳӯзҷ»е Ўд»ҘзұҢйӣҶжҲ°зҲӯиіҮйҮ‘гҖӮз”ұж–јйҰ¬жһ—е ЎеҹҺе Ўиў«з§»дәӨзөҰеғұеӮӯи»Қд»Ҙд»Јжӣҝд»–еҖ‘зҡ„е ұй…¬пјҢдёҰжңҖзөӮ移дәӨзөҰжіўиҳӯпјҢеӣ жӯӨйЁҺеЈ«еңҳе°Үе…¶еҹәең°йҒ·иҮіжЎ‘жҜ”дәһзҡ„жҹҜе°јж–Ҝе ЎгҖӮ  1466е№ҙзөҗжқҹеҚҒдёүе№ҙжҲ°зҲӯзҡ„гҖҠ第дәҢж¬ЎжүҳеҖ«е’Ңзҙ„гҖӢиҰҸе®ҡ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йҷӨиө”ж¬ҫ600дёҮи‘ӣзҫ…зҗӣд»ҘеӨ–пјҢйӮ„иҰҒеүІи®“иҘҝжҷ®йӯҜеЈ«дәҲжіўиҳӯзҺӢеңӢгҖӮиў«ж“Ҡж•—зҡ„йЁҺеЈ«еңҳж”ҫжЈ„дәҶе°Қж јдҪҶж–Ҝе…Ӣ/жқұжіўзҫҺжӢүе°јдәһе’Ңжө·зғҸе§Ҷи«ҫй ҳең°зҡ„д»»дҪ•ж¬ҠеҲ©иҰҒжұӮпјҢйҖҷдәӣй ҳеңҹиҲҮжіўиҳӯйҮҚж–°еҗҲдҪөд»ҘеҸҠеҹғе°”е®ҫпјҲеҹғзҲҫеёғйҡҶж јпјүе’Ң马жһ—е ЎпјҲйҰ¬зҲҫе Ўпјүең°еҚҖд»ҘеҸҠдё»ж•ҷдё»ж•ҷеҚҖз“ҰзҲҫзұідәһд№ҹиў«иӘҚзӮәжҳҜжіўиҳӯ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еҗҢжҷӮдҝқз•ҷдәҶжӯ·еҸІжӮ д№…зҡ„жҷ®йӯҜеЈ«зҡ„жқұйғЁй ҳеңҹпјҢдҪҶдҪңзӮәжіўиҳӯзҡ„е°Ғең°е’Ңдҝқиӯ·еңӢпјҢд№ҹиў«иӘҚзӮәжҳҜвҖңдёҖеҖӢдёҚеҸҜеҲҶеүІзҡ„вҖқжіўиҳӯзҺӢеңӢдёҚеҸҜеҲҶеүІ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гҖӮеҫһзҸҫеңЁй–Ӣе§ӢпјҢжҜҸдёҖеҖӢ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еӨ§еңҳй•·йғҪеҝ…й ҲеңЁдёҠд»»е…ӯеҖӢжңҲе…§е®ЈиӘ“ж•Ҳеҝ ж–јеңЁдҪҚзҡ„жіўиҳӯеңӢзҺӢпјҢеӨ§еӣўй•ҝжҲҗзӮәжіўиҳӯеңӢзҺӢе’ҢжіўиҳӯзҺӢеңӢзҡ„дәІзҺӢе’ҢйЎҫй—®гҖӮ дё–дҝ—ж”№еҲ¶1512е№ҙпјҢжқҘиҮӘеӢғе…°зҷ»е ЎйңҚдәЁзҙўеҖ«е®¶ж—Ҹзҡ„йҳҝе°”еёғйӣ·еёҢзү№иў«йҖүдёә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жҖ»еӣўй•ҝпјҢд»–жҳҜеӢғе…°зҷ»е ЎйҖүеёқдҫҜзҡ„иҝ‘иҰӘгҖӮжіўиҳӯ-жўқй “жҲ°зҲӯд№ӢеҫҢпјҢ當еӢғиҳӯзҷ»е Ўзҡ„йҳҝзҲҫдјҜзү№еӨ§еңҳй•·ж–ј1525е№ҙзҡҲдҫқдҝЎзҫ©е®—жҷӮ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е®Ңе…Ёиў«жҷ®йӯҜ士趕дёӢеҸ°гҖӮд»–е°ҮйЁҺеЈ«еңҳеү©йӨҳзҡ„жҷ®йӯҜеЈ«й ҳеңҹдё–дҝ—еҢ–пјҢдёҰз№јжүҝдәҶд»–зҡ„еҸ”еҸ”иҘҝеҗүж–Ҝи’ҷеҫ·дёҖдё–зҡ„еңӢзҺӢпјҢжіўиҳӯпјҢжҷ®йӯҜеЈ«е…¬еңӢдҪңзӮәжіўиҳӯзҺӢе®Өзҡ„еҖӢдәәйҷ„еәёзҡ„дё–иҘІж¬ҠеҲ©пјҢжҷ®йӯҜеЈ«ж•Ҳеҝ гҖӮжҷ®йӯҜеЈ«е…¬зҲөдҝқз•ҷдәҶе®ғзҡ„иІЁе№ЈгҖҒжі•еҫӢе’ҢдҝЎд»°гҖӮиІҙж—ҸдёҚеңЁдёӢиӯ°йҷўгҖӮ 1525е№ҙпјҢйҳҝзҲҫеёғйӣ·еёҢзү№е®Јеёғж”№дҝЎйҰ¬дёҒВ·и·Ҝеҫ·зҡ„дҝЎзҫ©е®—пјҢд»ҺиҖҢеҲҮж–ӯдәҶдёҺйӘ‘еЈ«еӣўеҗҚд№үдёҠзҡ„е®—дё»ж•ҷе®—зҡ„иҒ”зі»пјҢйҡҸеҗҺе®Јеёғе°ҮйЁҺеЈ«еңҳй ҳең°ж”№дёәжҷ®йІҒеЈ«е…¬еӣҪпјҢйҳҝе°”еёғйӣ·еёҢзү№иҮӘд»»жҷ®йІҒеЈ«е…¬зҲөгҖӮе„ҳз®Ў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еӨұеҺ»дәҶе°Қе…¶жүҖжңүжҷ®йӯҜеЈ«еңҹең°зҡ„жҺ§еҲ¶ж¬ҠпјҢдҪҶд»Қдҝқз•ҷдәҶе…¶еңЁзҘһиҒ–зҫ…йҰ¬еёқеңӢе’Ң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еўғе…§зҡ„й ҳеңҹпјҢе„ҳз®Ў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еҲҶж”Ҝдҝқз•ҷдәҶзӣёз•¶еӨ§зҡ„иҮӘжІ»ж¬ҠгҖӮиЁұеӨҡеёқеңӢиІЎз”ўеңЁ1524е№ҙиҮі1525е№ҙзҡ„еҫ·ж„Ҹеҝ—иҫІж°‘жҲ°зҲӯдёӯиў«жҜҖпјҢйҡЁеҫҢиў«ж–°ж•ҷи«ёдҫҜ沒收гҖӮеңЁ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жҲ°зҲӯжңҹй–“пјҢ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й ҳеңҹиў«й„°еңӢз“ңеҲҶпјӣ1561е№ҙпјҢ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еӨ§еӣўй•ҝе“ҘйҒ”В·еҮұзү№еӢ’е°ҮйЁҺеЈ«еңҳеңЁеҲ©жІғе°јдәһеҚ—йғЁзҡ„еұ¬ең°дё–дҝ—еҢ–пјҢеүөе»әдәҶеә«зҲҫиҳӯе…¬еңӢпјҢд№ҹжҳҜжіўиҳӯйҷ„еәёгҖӮ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1525е№ҙеӨұеҺ»жҷ®йІҒеЈ«еҫҢпјҢдё“жіЁдәҺ他们еңЁзҘһеңЈзҪ—马еёқеӣҪзҡ„иҙўдә§гҖӮз”ұдәҺ他们没жңүиҝһз»ӯзҡ„йўҶеңҹпјҢ他们ејҖеҸ‘дәҶдёҖдёӘдёүеұӮзҡ„иЎҢж”ҝзі»з»ҹпјҡең°дә§еҗҲ并дёәз”ұжҢҮжҢҘе®ҳпјҲKomturпјүз®ЎзҗҶзҡ„жҢҮжҢҘе®ҳгҖӮеҮ дёӘеҸёд»ӨйғЁеҗҲ并еҪўжҲҗдёҖдёӘз”ұең°еҢәжҢҮжҢҘе®ҳпјҲLandkomturпјүйўҶеҜјзҡ„иҫ–еҢәгҖӮ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жүҖжңүиҙўдә§йғҪйҡ¶еұһдәҺдҪҚдәҺе·ҙзү№жў…ж №зү№жө·е§Ҷзҡ„еӨ§еӣўй•ҝгҖӮ еҫ·ж„Ҹеҝ—жңү12дёӘиҫ–еҢәпјҡ
еңЁеҫ·ж„Ҹеҝ—жң¬еңҹд№ӢеӨ–жҳҜпјҡ
йӘ‘еЈ«еӣўйҖҗжёҗеӨұеҺ»дәҶеҜ№иҝҷдәӣең°дә§зҡ„жҺ§еҲ¶жқғпјҢзӣҙеҲ°1809е№ҙж—¶пјҢеҸӘеү©дёӢдәҶжў…ж №зү№жө·е§ҶеӨ§еӣўй•ҝзҡ„еёӯдҪҚгҖӮ 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еҲҶиЈӮзӮәдёүеЎҠпјҡжҷ®йӯҜеЈ«йЁҺеЈ«еңҳе’Ңз«ӢзӘ©е°јдәһйЁҺеЈ«еңҳиҝ…йҖҹж¶ҲдәЎпјҢ第дёүеЎҠеҫ·ж„Ҹеҝ—йЁҺеЈ«еңҳеңЁзҘһиҒ–зҫ…йҰ¬еёқеңӢеўғе…§еҸҲжҙ»еӢ•дәҶ300е№ҙгҖӮ1806е№ҙпјҢзҘһиҒ–зҫ…йҰ¬еёқеңӢи§Јй«”пјӣ1809е№ҙпјҢжі•еңӢзҡҮеёқжӢҝз ҙеҙҷи§Јж•ЈдҪңдёәеҶӣдәӢз»„з»Үзҡ„еҫ·ж„Ҹеҝ—йЁҺеЈ«еңҳгҖӮжӢҝз ҙеҙҷеҖ’еҸ°еҫҢпјҢеҫ·ж„Ҹеҝ—йЁҺеЈ«еңҳеҶҚеәҰеҫ©жҙ», дҪҶжҳҜиў«иҝ«дҫқйҷ„ж–је“Ҳеёғж–Ҝе ЎзҺӢжңқиҖҢеӯҳеңЁгҖӮ зҺ°д»Ј19дё–зәӘеӨ©дё»ж•ҷжңғз№јзәҢеӯҳеңЁж–јеҘ§ең°еҲ©еёқеңӢзөұжІ»зҡ„еҗ„йӮҰпјҢжӢҝз ҙеҙҷз„Ўжі•и§ёеҸҠгҖӮеҫһ1804е№ҙиө·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з”ұе“Ҳеёғж–Ҝе ЎзҺӢжңқзҡ„жҲҗе“Ўй ҳе°ҺгҖӮ е“Ҳеёғж–Ҝе ЎзҺӢжңқеҸҠе…¶зөұжІ»зҡ„еҘ§ең°еҲ©гҖҒи’Ӯзҫ…зҲҫгҖҒжіўеёҢзұідәһе’Ңе·ҙзҲҫе№№гҖӮ1918е№ҙеёқеңӢзҡ„еҙ©жҪ°зөҰйЁҺеЈ«еңҳеё¶дҫҶдәҶжҜҖж»…жҖ§зҡ„еҚұж©ҹгҖӮйӣ–然еңЁж–°зҡ„еҘ§ең°еҲ©е…ұе’ҢеңӢ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дјјд№Һжңүз”ҹеӯҳзҡ„еёҢжңӣпјҢдҪҶеңЁе“Ҳеёғж–Ҝе Ўй ҳеңҹзҡ„е…¶д»–иҲҠең°еҚҖпјҢдәәеҖ‘еӮҫеҗ‘ж–је°ҮйЁҺеЈ«еңҳиҰ–зӮәе“Ҳеёғж–Ҝе Ўе®¶ж—Ҹзҡ„жҰ®иӯҪйЁҺеЈ«еӢіз« гҖӮйҖҷжЁЈеҒҡзҡ„еҫҢжһңжҳҜжңүеҸҜиғҪ沒收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иІЎз”ўпјҢдҪңзӮәе“Ҳеёғж–Ҝе Ўе®¶ж—Ҹзҡ„иІЎз”ўгҖӮзӮәдәҶжӣҙжё…жҘҡең°еҚҖеҲҶпјҢеңЁ1923е№ҙпјҢ當жҷӮзҡ„еӨ§еӣўй•ҝгҖҒеҘ§ең°еҲ©йҷёи»Қе…ғеёҘгҖҒеҘ§ең°еҲ©еӨ§е…¬гҖҒе“Ҳеёғж–Ҝе ЎзҺӢжңқжҲҗе“ЎгҖҒ第дёҖ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°еүҚе’Ң第дёҖ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°жңҹй–“зҡ„зҸҫеҪ№йҷёи»ҚжҢҮжҸ®е®ҳжӯҗж №ж“ҒжңүдёҖеҖӢ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зү§её«и«ҫдјҜзү№В·е…ӢиҗҠеӣ еңЁз•¶жҷӮзҡ„еёғзҲҫи«ҫдё»ж•ҷйҒёиҲүдәҶд»–зҡ„еҠ©зҗҶпјҢ然еҫҢйҖҖдҪҚпјҢи®“дё»ж•ҷжҲҗзӮә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й«ҳзҙҡеӨ§еңҳй•·гҖӮ 20дё–зәӘз”ұж–јйҖҷдёҖиҲүжҺӘпјҢеҲ°1928е№ҙпјҢзҸҫе·ІзҚЁз«Ӣзҡ„еүҚе“Ҳеёғж–Ҝе Ўең°еҚҖйғҪжүҝиӘҚйҖҷеҖӢдҝ®жңғжҳҜдёҖеҖӢеӨ©дё»ж•ҷж•ҷеңҳгҖӮж•ҷеңҳжң¬иә«еј•е…ҘдәҶдёҖй …ж–°иҰҸеүҮпјҢи©ІиҰҸеүҮз”ұж•ҷе®—еәҮиӯ·еҚҒдёҖдё–ж–ј1929е№ҙжү№еҮҶпјҢж №ж“ҡи©ІиҰҸеүҮпјҢи©Іж•ҷеңҳзҡ„ж”ҝеәңеңЁжңӘдҫҶе°Үз”ұж•ҷеңҳзҡ„дёҖеҗҚж•ҷеЈ«жҺҢжҸЎпјҢе…¶жүҖеұ¬зңҒд»Ҫд№ҹжҳҜеҰӮжӯӨпјҢиҖҢе©ҰеҘідҝ®жңғе°ҮжңүеҘіжҖ§дёҠеҸёгҖӮ1936е№ҙпјҢеҘіжҖ§дҝ®жңғзҡ„зӢҖжіҒеҫ—еҲ°йҖІдёҖжӯҘжҫ„жё…пјҢдҝ®еҘіжңғиў«жҺҲдәҲдҝ®еҘіжңғжңҖй«ҳз®ЎзҗҶиҖ…дҪңзӮәжңҖй«ҳдё»жҢҒпјҢдҝ®еҘіжңғеңЁдҝ®еҘіжңғзҡ„зёҪз« дёӯд№ҹжңүд»ЈиЎЁгҖӮ йҖҷе®ҢжҲҗдәҶе°Ү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еӨ©дё»ж•ҷжңғдёӯеү©йӨҳзҡ„жқұиҘҝиҪүи®ҠзӮәзҸҫеңЁжӣҙеҗҚзӮәDeutscher OrdenпјҲвҖңеҫ·ж„Ҹеҝ—ж•ҷеӣўвҖқпјүзҡ„еӨ©дё»ж•ҷе®—ж•ҷдҝ®жңғгҖӮ йҖҷзЁ®йҮҚзө„е’ҢзІҫзҘһиҪүи®Ҡзҡ„е……ж»ҝеёҢжңӣзҡ„й–Ӣз«ҜеҸ—еҲ°дәҶеҫ·еңӢеңЁеңӢ家зӨҫжңғдё»зҫ©ж”ҝж¬ҠдёӢж“ҙејөеҜҰеҠӣзҡ„еҡҙйҮҚжү“ж“ҠгҖӮеңЁ1938е№ҙеҘ§ең°еҲ©иў«еҫ·еңӢеҗһдҪөд№ӢеҫҢпјҢеҗҢжЁЈеңЁ1939е№ҙжҚ·е…Ӣеңҹең°иў«еҗһдҪөеҫҢпјҢ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еңЁж•ҙеҖӢеӨ§еҫ·ж„Ҹеҝ—еёқеңӢиў«еҺӢеҲ¶пјҢзӣҙеҲ°еҫ·еңӢжҲ°ж•—гҖӮйҖҷдёҰжІ’жңүйҳ»жӯўеңӢ家зӨҫжңғдё»зҫ©иҖ…е°Үдёӯдё–зҙҖ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зҡ„еҪўиұЎз”Ёж–је®ЈеӮізӣ®зҡ„гҖӮ дәҢжҲҳеҗҺ ж„ҸеӨ§еҲ©зҡ„жі•иҘҝж–ҜзөұжІ»иҮӘ第дёҖ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°зөҗжқҹд»ҘеҗҺеҗһ并дәҶеҚ—и’Ӯзҫ…зҲҫпјҢйҖҷдёҰдёҚжҳҜдёҖеҖӢжңүеҲ©зҡ„з’°еўғпјҢдҪҶеңЁдәҢжҲҳзҡ„ж•өе°ҚиЎҢеӢ•зөҗжқҹеҫҢпјҢдёҖеҖӢзҸҫеңЁж°‘дё»зҡ„ж„ҸеӨ§еҲ©жҸҗдҫӣдәҶжӯЈеёёеҢ–зҡ„жўқ件пјҢ1947е№ҙеҘ§ең°еҲ©еҗҲжі•ең°е»ўйҷӨдәҶжҺЎеҸ–зҡ„жҺӘж–ҪйҒ•еҸҚе‘Ҫд»ӨдёҰжҒўеҫ©жІ’收зҡ„иІЎз”ўгҖӮе„ҳз®ЎеҸ—еҲ°еҚ—ж–ҜжӢүеӨ«е’ҢжҚ·е…Ӣж–Ҝжҙӣдјҗе…Ӣе…ұз”ўдё»зҫ©ж”ҝж¬Ҡзҡ„йҳ»ж’“пјҢйЁҺеЈ«еңҳзҸҫеңЁеӨ§й«”дёҠиғҪеӨ ж №ж“ҡе…¶еӮізөұе…ғзҙ й–Ӣеұ•жҙ»еӢ•пјҢеҢ…жӢ¬з…§йЎ§з—…дәәгҖҒиҖҒдәәе’Ңе…’з«ҘпјҢеҢ…жӢ¬еҫһдәӢж•ҷиӮІе·ҘдҪңпјҢеңЁж•ҷеҚҖе’ҢиҮӘе·ұзҡ„е…§йғЁеӯёзҝ’е ҙжүҖгҖӮ1957е№ҙпјҢзҫ…йҰ¬ж•ҷе»·зёҪжӘўеҜҹй•·еңЁзҫ…йҰ¬е»әз«ӢдәҶдёҖеҖӢдҪҸжүҖпјҢдҪңзӮәжңқиҒ–иҖ…е®ҝиҲҚгҖӮжҚ·е…Ӣж–Ҝжҙӣдјҗе…Ӣзҡ„жғ…жіҒйҖҗжјёеҘҪиҪүпјҢиҲҮжӯӨеҗҢжҷӮпјҢдёҖдәӣйЁҺеЈ«еңҳжҲҗе“Ўзҡ„иў«иҝ«жөҒж”ҫе°ҺиҮҙйЁҺеЈ«еңҳеңЁеҫ·еңӢйҮҚж–°е»әз«ӢдәҶдёҖдәӣйҒ©еәҰдҪҶе…·жңүжӯ·еҸІж„Ҹзҫ©зҡ„еҹәзӨҺгҖӮе°Өе…¶жҳҜе§җеҰ№еҖ‘пјҢзҚІеҫ—дәҶе№ҫеҖӢз«Ӣи¶ій»һпјҢеҢ…жӢ¬е°Ҳй–Җеӯёж Ўе’Ңе°ҚзӘ®дәәзҡ„з…§йЎ§пјҢ1953е№ҙпјҢеё•зҙ№зҡ„еҘ§еҸӨж–ҜдёҒж•ҷиҰҸиҒ–е°јеҸӨжӢүж•…еұ…жҲҗзӮәе§җеҰ№д№Ӣ家гҖӮе„ҳз®Ўд»Ҙ1929е№ҙж”№йқ©иҰҸеүҮзӮәд»ЈиЎЁзҡ„йҮҚе»әе·Іе°ҮйЁҺеЈ«зӯүйЎһеҲҘж“ұзҪ®дёҖж—ҒпјҢдҪҶйҡЁи‘—жҷӮй–“зҡ„жҺЁз§»пјҢеӨ–иЎҢдәәиҮӘзҷјең°еҸғиҲҮ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дҪҝеҫ’е·ҘдҪңпјҢе°ҺиҮҙд»–еҖ‘д»ҘзҸҫд»ЈеҢ–зҡ„еҪўејҸиӨҮиҲҲпјҢйҖҷдёҖзҷјеұ•з”ұж•ҷе®—дҝқзҘҝе…ӯдё–ж–ј1965е№ҙжӯЈејҸзўәз«ӢгҖӮ е®ҳж–№еҗҚзЁұзӮәвҖң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ҫ·ж„Ҹеҝ—иҒ–з‘ӘеҲ©дәһд№Ӣ家зҡ„е…„ејҹжңғвҖқпјҢе„ҳз®ЎиҮӘжҲҗдёҖж јпјҢдҪҶд»ҠеӨ©зҡ„йЁҺеЈ«еңҳз„Ўз–‘жҳҜдёҖеҖӢеӨ©дё»ж•ҷе®—ж•ҷеңҳй«”гҖӮе®ғзҡ„з”ҹжҙ»е’Ңжҙ»еӢ•зҡ„еҗ„зЁ®зү№еҫөи®“дәәжғіиө·еғ§дҫ¶е’Ңд№һдёҗзҡ„зү№еҫөгҖӮе…¶ж ёеҝғжҳҜеҫһдәӢиҺҠеҡҙе®—ж•ҷиҒ·жҘӯзҡ„ж•ҷеЈ«пјҢд»ҘеҸҠеҫһдәӢж°ёд№…з°Ўе–®иҒ·жҘӯзҡ„е№ідҝЎеҫ’е…„ејҹгҖӮдҝ®жңғд№ҹжҳҜдҝ®еҘіжңғ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еңЁеҘ№еҖ‘иҮӘе·ұзҡ„зөҗж§Ӣе…§ж“Ғжңүе…§йғЁиҮӘжІ»ж”ҝеәңпјҢдҪҶеңЁдҝ®жңғзҡ„зёҪз« дёӯжңүд»ЈиЎЁгҖӮд»–еҖ‘зҡ„зөӮжҘөдёҠеҸёжҳҜжңҖй«ҳзөұеёҘгҖӮеӨ§зҙ„100еҗҚеӨ©дё»ж•ҷзҘһзҲ¶е’Ң200еҗҚдҝ®еҘіеҲҶзӮәдә”еҖӢзңҒпјҢеҚіеҘ§ең°еҲ©гҖҒеҚ—и’Ӯзҫ…зҲҫ-ж„ҸеӨ§еҲ©гҖҒж–Ҝжҙӣж–Үе°јдәһгҖҒеҫ·еңӢгҖҒжҚ·е…Ӣ-ж–Ҝжҙӣдјҗе…ӢгҖӮдҝ®еЈ«дё»иҰҒжҸҗдҫӣзІҫзҘһжҢҮе°ҺпјҢиҖҢдҝ®еҘідё»иҰҒз…§йЎ§з—…дәәе’ҢиҖҒдәәгҖӮиЁұеӨҡзҘһзҲ¶й—ңеҝғеҫ·иӘһзӨҫеҚҖгҖӮ з»„з»Үз»“жһ„жһ¶и®ҫж•ҷеӣўжҖ»и®®дјҡж•ҷеӣўжҖ»и®®дјҡпјҲеҫ·иҜӯпјҡGeneralkapitelпјүжҳҜжүҖжңүзү§еёҲгҖҒйӘ‘еЈ«е’ҢеҗҢзҲ¶ејӮжҜҚе…„ејҹпјҲеҫ·иҜӯпјҡHalbbrГјderпјүзҡ„йӣҶеҗҲгҖӮз”ұдәҺйӣҶз»“жҲҗе‘ҳзҡ„еҗҺеӢӨй—®йўҳпјҢ他们еҲҶж•ЈеңЁеҫҲиҝң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еҸӘжңүиҫ–еҢәе’ҢеҸёд»ӨйғЁзҡ„д»ЈиЎЁиҒҡйӣҶеңЁдёҖиө·з»„жҲҗжҖ»з« гҖӮжҖ»з« и®ҫи®ЎдёәжҜҸе№ҙдёҫиЎҢдёҖж¬Ўдјҡи®®пјҢдҪҶдјҡи®®йҖҡеёёд»…йҷҗдәҺйҖүдёҫж–°зҡ„е®—еёҲгҖӮ ж•ҷеӣўжҖ»и®®дјҡзҡ„еҶіе®ҡеҜ№иҜҘе‘Ҫд»Өзҡ„еӨ§е§”е‘ҳдјҡжҲҗе‘ҳе…·жңүзәҰжқҹеҠӣгҖӮ еӨ§еӣўй•ҝеӨ§еӣўй•ҝпјҲHochmeisterпјүжҳҜиҜҘе‘Ҫд»Өзҡ„жңҖй«ҳе®ҳе‘ҳгҖӮзӣҙеҲ°1525е№ҙпјҢд»–жүҚиў«ж•ҷеӣўжҖ»и®®дјҡйҖүдёҫгҖӮд»–жӢҘжңүдёҖдёӘж•ҷзҡҮеӣҪзҡ„з»ҹжІ»иҖ…зә§еҲ«пјҢ并且еңЁ 1466 е№ҙд№ӢеүҚдёҖзӣҙжҳҜжҷ®йІҒеЈ«зҡ„дё»жқғгҖӮе°Ҫз®ЎжңүеҰӮжӯӨй«ҳзҡ„жӯЈејҸиҒҢдҪҚпјҢдҪҶеңЁе®һи·өдёӯпјҢд»–еҸӘжҳҜе№ізӯүдёӯзҡ„第дёҖдәәгҖӮ еӨ§е§”е‘ҳдјҡеӨ§е§”е‘ҳдјҡпјҲеҫ·иҜӯпјҡGroГҹgebietigerпјүжҳҜз”ұеӨ§еӣўй•ҝд»»е‘Ҫзҡ„е…·жңүж•ҙдёӘе‘Ҫд»ӨиғҪеҠӣзҡ„й«ҳзә§еҶӣе®ҳгҖӮжңүдә”дёӘиҒҢдҪҚгҖӮ
еӨ§еңҳй•·е…„ејҹдјҡж—¶жңҹ
 еҶӣдәӢж•ҷеӣўж—¶жңҹ
ж”№еҲ¶д№ӢеҗҺ
зҺ°д»Ј
зҺ°д»ЈиҚЈиӘүйӘ‘еЈ«
ең–йӣҶ
еҫҢдё–и©•еғ№ 1902е№ҙпјҢеҫ·еңӢзҡҮеёқеЁҒе»үдәҢдё–иә«и‘—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еғ§дҫ¶зҡ„иЈқжқҹпјҢеңЁйҮҚе»әзҡ„йҰ¬е°”е ЎеҹҺе ЎдёӯзҲ¬жЁ“жўҜпјҢдҪңзӮәеҫ·ж„Ҹеҝ—еёқеңӢж”ҝзӯ–зҡ„иұЎеҫөгҖӮ еҫ·еңӢжӯ·еҸІеӯёе®¶жө·еӣ йҮҢеёҢВ·йҰ®В·зү№иіҙиҢЁе…ӢдҪҝз”Ё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еҪўиұЎдҫҶе®ЈеӮіиҰӘеҫ·е’ҢеҸҚжіўиҳӯзҡ„иЁҖи«–гҖӮиЁұеӨҡеҫ·еңӢдёӯз”ўйҡҺзҙҡж°‘ж—Ҹдё»зҫ©иҖ…жҺЎз”ЁдәҶйҖҷзЁ®ж„ҸиұЎеҸҠе…¶з¬ҰиҷҹгҖӮеңЁйӯҸз‘Әе…ұе’ҢеңӢжңҹй–“пјҢйҖҷзЁ®жҖ§иіӘзҡ„еҚ”жңғе’Ңзө„з№”зӮәзҙҚзІ№еҫ·еңӢзҡ„еҪўжҲҗеҘ е®ҡдәҶеҹәзӨҺгҖӮ еңЁз¬¬дәҢ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°д№ӢеүҚе’Ңжңҹй–“пјҢзҙҚзІ№е®ЈеӮіе’Ңж„ҸиӯҳеҪўж…Ӣ經常дҪҝз”Ё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еҪўиұЎпјҢеӣ зӮәзҙҚзІ№и©Ұең–е°Ү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иЎҢзӮәжҸҸз№ӘжҲҗзҙҚзІ№еҫҒжңҚз”ҹеӯҳеҚҖзҡ„е…ҲиЎҢиҖ…гҖӮжө·еӣ йҮҢеёҢВ·еёҢе§ҶиҗҠи©Ұең–е°Үй»ЁиЎӣи»ҚзҗҶжғіеҢ–зӮә20дё–зҙҖдёӯдё–зҙҖеҶӣдәӢж•ҷеӣўзҡ„иҪүдё–гҖӮ然иҖҢе„ҳз®ЎеңЁзҙҚзІ№е®ЈеӮідёӯжҸҗеҲ°дәҶ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жӯ·еҸІпјҢдҪҶйЁҺеЈ«еңҳжң¬иә«еңЁ1938е№ҙиў«е»ўйҷӨпјҢе…¶жҲҗе“ЎеҸ—еҲ°еҫ·еңӢ當еұҖзҡ„иҝ«е®ігҖӮйҖҷдё»иҰҒжҳҜеӣ зӮәеёҢзү№еӢ’е’ҢеёҢе§ҶиҗҠзӣёдҝЎпјҢзёұи§Җжӯ·еҸІпјҢеӨ©дё»ж•ҷзҡ„и»ҚдәӢе®—ж•ҷе‘Ҫд»ӨдёҖзӣҙжҳҜзҫ…йҰ¬ж•ҷе»·зҡ„е·Ҙе…·пјҢеӣ жӯӨе°ҚзҙҚзІ№ж”ҝж¬Ҡж§ӢжҲҗеЁҒи„…гҖӮеёҢзү№еӢ’е°Үд»–зҡ„еҫ·еңӢйЁҺеЈ«еңҳе»әз«ӢеңЁжўқй “йЁҺеЈ«еңҳзҡ„еҹәзӨҺдёҠ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еӨ§еңҳй•·зҡ„зҰ®е„ҖеҫҪз« жң¬иә«пјҢе„ҳз®Ўд»–еҖ‘е»ўйҷӨдәҶдёҠиҝ°е‘Ҫд»ӨгҖӮ жіўиҳӯзҡ„и§Ҷи§’еҜ№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дәүи®®жҖ§иҜ„д»·е§ӢдәҺ19дё–зәӘеҲқжңҹпјҢиҝҷдёҖж—¶жңҹдёҖж–№йқўйҮҚж–°еҸ‘зҺ°е№¶жөӘжј«еҢ–дёӯдё–зәӘ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жіўе…°жӯЈеӨ„дәҺиў«еҚ йўҶдёҺжҢҒз»ӯз“ңеҲҶзҡ„зҠ¶жҖҒгҖӮиҮӘ1850е№ҙиө·пјҢиҝҷз§Қж°ӣеӣҙеҸ‘еұ•дёәдёҖз§ҚвҖңжӣҝд»ЈжҖ§зҡ„ж–ҮеҢ–ж–—дәүвҖқгҖӮ[10]дәүи®әжңҖеҲқеҸ‘з”ҹеңЁжіўе…°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дёҺжҷ®йІҒеЈ«-еҫ·еӣҪеҺҶеҸІеӯҰ家д№Ӣй—ҙпјҢ1860е№ҙд»ҘеҗҺпјҢжіўе…°зҡ„еҺҶеҸІеӯҰиҖ…д№ҹжӯЈејҸеҠ е…Ҙи®әжҲҳгҖӮ жіўе…°еҮәзүҲзү©жҢҮжҺ§йӘ‘еЈ«еӣўеҜ№жҷ®йІҒеЈ«дәәе®һж–ҪдәҶз§Қж—ҸзҒӯз»қ[11]并жү§иЎҢжҜ«ж— иҠӮеҲ¶зҡ„жү©еј ж”ҝзӯ–пјҢ[12]иҖҢеҫ·еӣҪеҺҶеҸІеӯҰ家еҲҷе°ҶиҜҘйӘ‘еЈ«еӣўжҸҸз»ҳдёәвҖңж—ҘиҖіжӣјж–ҮеҢ–зҡ„дј ж’ӯиҖ…вҖқгҖӮ иҝҷеңәдәүи®әеңЁеҫ·еӣҪж–№йқўжҢҒз»ӯиҮі1945е№ҙпјҢеңЁжіўе…°ж–№йқўеҲҷеңЁ1989е№ҙеүҚиҷҪжңүзј“е’ҢдҪҶдҫқ然еӯҳеңЁгҖӮжіўе…°еҺҶеҸІеӯҰ家жүҳйҰ¬ж–ҜВ·жүҳзҲҫеёғиҢІиҝҷж ·жҖ»з»“йҒ“пјҡвҖңеңЁеҫ·еӣҪпјҢд»ҺеёқеӣҪе»әз«ӢеҲ°зәізІ№еӣҪ家еҙ©жәғзҡ„ж—¶жңҹ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дәәж–ҮеӯҰ科гҖҒе®Јдј дёҺеҪ“д»Јж”ҝжІ»дёӯдёҚж–ӯиў«еј•з”ЁпјӣеңЁжіўе…°пјҢиҝҷз§ҚзҺ°иұЎжҢҒз»ӯиҮі1989е№ҙй“Ғ幕еҖ’еЎҢгҖӮвҖқ[13] иҝҷеңәжіўе…°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еҜ№еҚ йўҶиҖ…зҡ„еҲқжңҹи®әдәүе§ӢдәҺж–ҮеӯҰйўҶеҹҹгҖӮ1826е№ҙпјҢдәҡеҪ“В·еҜҶиҢЁеҮҜз»ҙеҘҮеҸ‘иЎЁдәҶй•ҝиҜ—гҖҠеә·жӢүеҫ·В·з“ҰдјҰзҪ—еҫ·гҖӢпјҢеҖҹз”ЁеҺҶеҸІйҡҗе–»жқҘжү№иҜ„дҝ„зҪ—ж–ҜеҜ№жіўе…°зҡ„й«ҳеҺӢж”ҝзӯ–пјҢд»ҘйҒҝејҖжІҷдҝ„зҡ„е®ЎжҹҘеҲ¶еәҰгҖӮд»–е°Ҷжіўдҝ„еҶІзӘҒзҪ®дәҺдёӯдё–зәӘиҲһеҸ°пјҢ并д»Ҙйҳҙжҡ—зҡ„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ҪўиұЎд»ЈжӣҝжІҷдҝ„еҚ йўҶиҖ…гҖӮ[14]19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пјҢеҲ©жІғеӨ«еҺҶеҸІеӯҰ家еҚЎзҪ—е°”В·жІҷдјҠиҜәе“Ҳж’°еҶҷеҺҶеҸІеҸҷдәӢгҖҠйӣ…зӣ–жІғдёҺйӣ…еҫ·з»ҙеҠ гҖӢпјҢи®©еҮ д»Јжіўе…°дәәеҪўжҲҗеҜ№иҜҘеҶІзӘҒзҡ„ж°‘ж—Ҹи®ӨзҹҘгҖӮ[15]1874е№ҙеҮәзүҲзҡ„жҳҫе…Ӣз»ҙж”ҜгҖҠеҚҒеӯ—еҶӣйӘ‘еЈ«гҖӢпјҲKrzyЕјacyпјүеҲҷе°ҶйӘ‘еЈ«еӣўжҸҸз»ҳдёәеҚҒи¶ізҡ„жҒ¶йӯ”гҖӮ[16] д»Һ1865е№ҙиө·пјҢиў«и§Ҷдёәжіўе…°еҺҶеҸІеӯҰеҘ еҹәдәәзҡ„жІғдјҠеҲҮиө«В·иӮҜзҗҙж–Ҝеҹәе®Јз§°пјҢеҫ·ж„Ҹеҝ—зҡ„з»ҹжІ»еҸӘдёәж–ҜжӢүеӨ«дәәеёҰжқҘвҖңиӢҰйҡҫдёҺеҘҙеҪ№вҖқгҖӮиҝҷдёҖи§ӮзӮ№е°ҶйӘ‘еЈ«еӣўеЎ‘йҖ дёәвҖңз”ұзҠҜзҪӘиғҪйҮҸй©ұеҠЁгҖҒд»ҘжҡҙеҠӣеҫҒжңҚжҲ–еҲ©з”ЁеҪ“ең°ж–ҜжӢүеӨ«з»ҹжІ»иҖ…зҡ„еӨ©зңҹиҖҢдёңжү©зҡ„жқЎйЎҝдё»д№үвҖқпјҢеҗҺжқҘеңЁжіўе…°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зҡ„еҮәзүҲзү©дёӯиў«иҝӣдёҖжӯҘи§ЈйҮҠдёәз§Қж—ҸзҒӯз»қжҲ–зҒӯз»қж”ҝзӯ–пјҲжіўе…°иҜӯпјҡwytДҷpienieпјүгҖӮ19дё–зәӘжіўе…°з»ҳз”»д№ҹж·ұеҸ—иҝҷдёҖж°‘ж—ҸеҸҷдәӢ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йҖҡеёёиў«жҸҸз»ҳдёәе—ңиЎҖгҖҒж®Ӣжҡҙзҡ„ж•ҢдәәгҖӮдҫӢеҰӮжІғдјҠеҲҮиө«В·ж је°”жқҫпјҲWojciech GersonпјүдәҺ1875е№ҙеҲӣдҪңзҡ„еҺҶеҸІз”»дҪңдёӯпјҢйӘ‘еЈ«еҪўиұЎжһҒдёәиҙҹйқўгҖӮеҚідҪҝеңЁеҪ“д»Јзҡ„жіўе…°еҺҶеҸІйҮҚжј”жҙ»еҠЁдёӯпјҢеҰӮ2010е№ҙеңЁиҗЁиҜәе…ӢпјҚе§Ҷж—Ҙж јд№Ңеҫ·пјҲMrzygЕӮГіdпјүдёҫиЎҢзҡ„жҙ»еҠЁдёӯ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д»Қиў«дҪңдёәиұЎеҫҒжҖ§еҪўиұЎеҮәзҺ°гҖӮ 1871е№ҙеҫ·ж„Ҹеҝ—еёқеӣҪжҲҗз«ӢеҗҺпјҢжҷ®йІҒеЈ«ең°еҢәзҡ„ж—ҘиҖіжӣјеҢ–ж”ҝзӯ–иҝӣдёҖжӯҘжҝҖиө·жіўе…°дәәзҡ„еҸҚж„ҹгҖӮеңЁ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йҖҗжёҗй«ҳж¶Ёзҡ„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жіўе…°зӨҫдјҡејҖе§Ӣд»Ҙ1410е№ҙзҡ„ж јдјҰз“Ұе°”еҫ·жҲҳеҪ№дҪңдёәж°‘ж—Ҹи®°еҝҶзҡ„ж ёеҝғиұЎеҫҒд№ӢдёҖпјҢжҜҸйҖўжҲҳеҪ№зәӘеҝөж—ҘдҫҝдёҫиЎҢеӨ§и§„жЁЎзәӘеҝөжҙ»еҠЁ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жіўе…°еҺҶеҸІз»ҳз”»д№ҹиҝӣе…Ҙз№ҒиҚЈж—¶жңҹпјҢи®ёеӨҡдҪңе“ҒжҸҸз»ҳжіўе…°жҲҳиғ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ңәжҷҜгҖӮе…¶дёӯжңҖе…·д»ЈиЎЁжҖ§зҡ„дёәжү¬В·й©¬зү№дјҠ科зҡ„е·Ёе№…з”»дҪңгҖҠж јдјҰз“Ұе°”еҫ·д№ӢжҲҳгҖӢпјҢиұЎеҫҒжіўе…°еҜ№вҖңеӮІж…ўзҡ„еҫ·ж„Ҹеҝ—зІҫзҘһвҖқзҡ„иғңеҲ©гҖӮ жҳҫе…Ӣз»ҙж”Ҝзҡ„е°ҸиҜҙгҖҠеҚҒеӯ—еҶӣйӘ‘еЈ«гҖӢд№ҹд»ҘеҺҶеҸІе°ҸиҜҙзҡ„еҪўејҸејәеҢ–дәҶиҝҷдёҖеҸҷдәӢпјҢиҜҘдҪңе“Ғиў«зҝ»иҜ‘жҲҗеӨҡз§ҚиҜӯиЁҖпјҢ并е°ҶйӘ‘еЈ«еӣўеЎ‘йҖ жҲҗйҒ“еҫ·иҙҘеқҸгҖҒеҪўиұЎеҸҜжҶҺзҡ„йӣҶдҪ“гҖӮ 1918е№ҙе»әз«Ӣ波兰第дәҢе…ұе’ҢеӣҪеҗҺпјҢжіўе…°еҺҶеҸІеӯҰз•ҢејҖе§ӢйҮҚж–°е®Ўи§Ҷ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җҲжі•жҖ§гҖӮеӯҰиҖ…иҙЁз–‘гҖҠе…ӢйІҒж–Ҫз»ҙиҢЁжқЎзәҰгҖӢзҡ„зңҹе®һжҖ§д»ҘеҸҠ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жіўзҪ—зҡ„жө·ең°еҢәзҡ„жӯЈеҪ“жҖ§гҖӮйғЁеҲҶеӯҰиҖ…еј•з”Ёеҫ·еӣҪеҸІеӯҰ家жө·еӣ йҮҢеёҢВ·еҶҜВ·зү№иө–иҢЁе…Ӣ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е°ҶйӘ‘еЈ«еӣўеҜ№жҷ®йІҒеЈ«дәәзҡ„еҫҒжңҚиЎҢдёәе®ҡжҖ§дёәз§Қж—ҸзҒӯз»қпјҢ并е°Ҷ1308е№ҙеҚ йўҶжіўзҫҺйӣ·еҲ©дәҡи§ҶдёәеҜ№вҖңжіўе…°еӣәжңүйўҶеңҹвҖқзҡ„дҫөеҚ гҖӮ е°Ҫз®ЎзҺ°д»ЈеӯҰжңҜз•ҢеҜ№вҖңдёӯдё–зәӘз§Қж—ҸзҒӯз»қвҖқиҝҷдёҖиҜҙжі•жҢҒжү№иҜ„жҖҒеәҰпјҢдҪҶеңЁ20дё–зәӘжіўе…°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е…ҙиө·еҸҠеҫ·жіўзҙ§еј е…ізі»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е…ідәҺйӘ‘еЈ«еӣўвҖңж¶ҲзҒӯжҷ®йІҒеЈ«дәәвҖқзҡ„иЎЁиҝ°еңЁйғЁеҲҶйҖҡдҝ—еҸІеӯҰдҪңе“Ғдёӯд»ҚжңүеҮәзҺ°гҖӮ然иҖҢпјҢеӨҡж•°зҺ°д»ЈеҺҶеҸІеӯҰиҖ…и®ӨдёәпјҢз”ЁвҖңз§Қж—ҸзҒӯз»қвҖқдёҖиҜҚжқҘжҸҸиҝ°дёӯдё–зәӘ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иЎҢдёәжҳҜйқһеҺҶеҸІзҡ„гҖҒзјәд№Ҹж–ҮзҢ®иҜҒжҚ®ж”ҜжҢҒзҡ„еӨёеј иҜҙжі•гҖӮйӘ‘еЈ«еӣўж—ўжңӘи®ЎеҲ’жҖ§зҒӯз»қеҪ“ең°дәәпјҢд№ҹжңӘзі»з»ҹжҖ§жҺЁиЎҢиҜӯиЁҖдёҺж–ҮеҢ–зҡ„жҠ№йҷӨгҖӮ[17] зәізІ№еҫ·еӣҪеӨұиҙҘеҗҺпјҢжіўе…°е…ұдә§е…ҡж”ҝжқғеҖҹз”ЁвҖңж јдјҰз“Ұе°”еҫ·1410е№ҙ=жҹҸжһ—1945е№ҙвҖқзҡ„е®Јдј йҖ»иҫ‘пјҢејәеҢ–еҜ№еҫ·иғңеҲ©зҡ„иұЎеҫҒж„Ҹд№үгҖӮеҶ·жҲҳж—¶жңҹзҡ„е®Јдј жӣҙе°Ҷ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ӯүеҗҢдәҺвҖңиҘҝеҫ·еҶӣеӣҪдё»д№үдёҺеӨҚд»Үдё»д№үвҖқзҡ„иұЎеҫҒпјҢејәи°ғжіўе…°дёҺиӢҸиҒ”д№Ӣй—ҙзҡ„жіӣж–ҜжӢүеӨ«еӣўз»“гҖӮ[18] жіўе…°зӨҫдјҡеҜ№иҝҷдёҖеҺҶеҸІи®°еҝҶзҡ„жғ…ж„ҹи®ӨеҗҢдёҖзӣҙ延з»ӯиҮід»ҠгҖӮдҫӢеҰӮеңЁ2008е№ҙ欧жҙІи¶ізҗғй”Ұж ҮиөӣеүҚеӨ•пјҢжіўе…°е°ҸжҠҘеҲҠзҷ»еҫ·еӣҪйҳҹй•ҝиҝҲе…Ӣе°”В·е·ҙжӢүе…Ӣиә«з©ҝ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жңҚиЈ…зҡ„жј«з”»пјҢй…Қд»ҘвҖңеҶҚзҺ°ж јдјҰз“Ұе°”еҫ·вҖқзҡ„еҸЈеҸ·пјҢд»ҘжҝҖеҸ‘ж°‘ж—Ҹжғ…з»ӘгҖӮиҝҷз§ҚжүӢжі•иҷҪйқһдё»жөҒпјҢдҪҶеҒ¶е°”д»ҚеҮәзҺ°еңЁеӘ’дҪ“дёӯгҖӮ 1970е№ҙд»Јиө·пјҢйҡҸзқҖиҘҝеҫ·еЁҒеҲ©В·еӢғе…°зү№ж”ҝеәңжҺЁиЎҢдёңж–№ж”ҝзӯ–пјҢеҫ·жіўе…ізі»зј“е’ҢпјҢеҸҢж–№еӯҰиҖ…еҗҲдҪңејҖеұ•еҺҶеҸІиҜҫжң¬е®Ўи®ўе·ҘдҪңгҖӮ1977е№ҙжҲҗз«Ӣзҡ„иҒ”еҗҲж•ҷ科ж–Үз»„з»Үж•ҷ科д№Ұ委е‘ҳдјҡжҺЁеҠЁдёӨеӣҪеңЁеҺҶеҸІи®°еҝҶдёҠзҡ„зӣёдә’зҗҶи§ЈпјҢд№ҹдҝғдҪҝжіўе…°еҜ№йӘ‘еЈ«еӣўеҪўиұЎзҡ„йҮҚж–°е®Ўи§Ҷи¶Ӣеҗ‘е®ўи§ӮгҖӮ д»Ҡж—Ҙзҡ„жіўе…°д»Қ然еңЁжҜҸе№ҙ7жңҲдёӯж—¬дёҫиЎҢжҲҳеҪ№зәӘеҝөйҮҚжј”жҙ»еҠЁпјҢдёҚд»…жңүжіўе…°е’Ңз«Ӣйҷ¶е®ӣзҡ„еӣўдҪ“еҸӮеҠ пјҢд№ҹжңүеҫ·еӣҪеӣўдҪ“д»ҘеҺҶеҸІе’Ңи§Јдёәзӣ®зҡ„еҠ е…ҘгҖӮ2010е№ҙзәӘеҝөжҙ»еҠЁдёҠ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ӣўй•ҝеёғйІҒиҜәВ·жҷ®жӢүзү№еҮәеёӯ并зҢ®иҠұиҮҙиҫһпјҢиұЎеҫҒдёӨеӣҪж°‘ж—Ҹе’Ңи§ЈгҖӮ дҝ„зҪ—ж–Ҝзҡ„и§Ҷи§’ еңЁдҝ„зҪ—ж–ҜпјҢдёҺ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…ұеҗҢеҺҶеҸІзҡ„еӨ„зҗҶе…·жңүзү№ж®ҠиғҢжҷҜгҖӮиө·зӮ№жҳҜ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жіўзҪ—зҡ„жө·еҢ—йғЁдёҺдҝ„зҪ—ж–ҜеҠҝеҠӣзҡ„зӣҙжҺҘеҶІзӘҒпјҢе°Өе…¶д»Ҙ1242е№ҙеҶ°ж№–жҲҳеҪ№дёәй«ҳжҪ®гҖӮ[19]е°Ҫз®ЎзҺ°д»ЈеҺҶеҸІеӯҰ家еӨҡе°ҶжӯӨжҲҳи§ҶдёәдёҖж¬ЎиҫғеӨ§и§„жЁЎзҡ„е°ҸеҶІзӘҒпјҢ[20]пјҢдёӯдё–зәӘзҡ„дҝ„еӣҪзј–е№ҙеҸІеҚҙе°Ҷе…¶зҘһеҢ–дёәеӨ©дё»ж•ҷдјҡдёҺдҝ„зҪ—ж–ҜдёңжӯЈж•ҷдјҡд№Ӣй—ҙзҡ„еҶіжҲҳд№ӢеҪ№гҖӮ[21] йҖҡиҝҮиҝҷз§ҚеҺҶеҸІи§ЈиҜ»пјҢдҝ„еӣҪеҸІеӯҰд№ҹеҫ—д»Ҙж·ЎеҢ–дҝ„зҪ—ж–ҜиҜёдҫҜеңЁеҜ№жҠ—йҮ‘еёҗи’ҷеҸӨиҝҮзЁӢдёӯзҡ„иҙҘз»©гҖӮ[22]然иҖҢпјҢдёҺи’ҷеҸӨдәәзӣёжҜ”пјҢдҝ„зҪ—ж–ҜдәәеҜ№еҫ·еӣҪдәәзҡ„жҠөжҠ—жӣҙдёәжҝҖзғҲпјҢе…¶еҺҹеӣ еңЁдәҺи’ҷеҸӨдәә并дёҚе№Іж¶үдёңжӯЈж•ҷдҝЎд»°е’Ңз”ҹжҙ»ж–№ејҸпјҢд»…еҫҒ收иҙЎиөӢпјӣиҖ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еҲҷеңЁж•ҷзҡҮж”ҜжҢҒдёӢпјҢд»Ҙе®—ж•ҷдёәеҗҚпјҢдјҒеӣҫж”№е®—з”ҡиҮіж¶ҲзҒӯдёңжӯЈж•ҷеҫ’иҝҷдёҖвҖңејӮз«ҜвҖқгҖӮ йҷӨеҶ°ж№–жҲҳеҪ№еӨ–пјҢ1268е№ҙзҡ„йҹӢжЈ®е ЎжҲ°еҪ№дәҰиў«дҝ„зҪ—ж–ҜеҸІеӯҰз•Ңи§ҶдёәйҮҚиҰҒиғңеҲ©гҖӮеҗҢж ·пјҢ1410е№ҙеқҰиғҪе ЎжҲҳеҪ№д№ҹеҸ—еҲ°дҝ„зҪ—ж–Ҝзј–е№ҙеҸІзҡ„йҮҚи§ҶпјҢеӣ дёәеҸӮдёҺиҜҘжҲҳзҡ„зҷҪдҝ„зҪ—ж–ҜеҶӣеӣўиў«иөӢдәҲе…ій”®жҖ§зҡ„жҲҳеҪ№иҙЎзҢ®гҖӮ[23] еҲ°дәҶ1930е№ҙд»ЈпјҢеңЁиӢҸиҒ”дёҺзәізІ№еҫ·еӣҪзҡ„ж„ҸиҜҶеҪўжҖҒеҜ№жҠ—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ҪўиұЎиў«иөӢдәҲж–°зҡ„ж”ҝжІ»еҗ«д№үпјҢжҲҗдёәеңЁдҝ„зҪ—ж–Ҝеңҹең°дёҠзҡ„ж— жғ…дҫөз•ҘиҖ…е’ҢзәізІ№дё»д№үзҡ„еүҚиә«иұЎеҫҒгҖӮ[24]иҝҷдёҖи§ЈйҮҠзҡ„е…ёеһӢиүәжңҜеҶҚзҺ°дҫҝжҳҜи°ўе°”зӣ–В·зҲұжЈ®ж–ҜеқҰжү§еҜјзҡ„з”өеҪұгҖҠдәҡеҺҶеұұеӨ§В·ж¶…еӨ«ж–ҜеҹәгҖӢпјҢиҜҘзүҮеңЁ1941иҮі1945е№ҙй—ҙзҡ„иӢҸеҫ·жҲҳдәүдёӯжҲҗдёәеҸҚеҫ·ж”ҝжІ»е®Јдј зҡ„йҮҚиҰҒе·Ҙе…·гҖӮ[25] зӣҙеҲ°иӢҸиҒ”и§ЈдҪ“еүҚпјҢе®ҳж–№еҜ№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и§ЈиҜ»е§Ӣз»ҲжңӘи„ұзҰ»дёҠиҝ°жЎҶжһ¶гҖӮ[26]зӣҙиҮід»Ҡж—ҘпјҢдёҖдәӣдҝ„зҪ—ж–Ҝ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еӣўдҪ“д»ҚеқҡжҢҒи®Өдёә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жҳҜзҪ—马еӨ©дё»ж•ҷдјҡдёҺеҫ·еӣҪе°Ғе»әеҠҝеҠӣдҫөз•Ҙдҝ„зҪ—ж–ҜйўҶеңҹгҖҒж¶ҲзҒӯдёңжӯЈж•ҷзҡ„е·Ҙе…·гҖӮ жҷ®йІҒеЈ«дёҺеҫ·еӣҪзҡ„и§Ҷи§’ еңЁж–°ж•ҷжҷ®йІҒеЈ«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ҪўиұЎй•ҝжңҹд»ҘжқҘ并дёҚжӯЈйқўпјҢе°Өе…¶еҸ—еҲ°15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дёҺжҷ®йІҒеЈ«зӯүзә§йҳ¶еұӮзҲҶеҸ‘зҡ„еҚҒдёүе№ҙжҲҳдәүеҪұе“ҚпјҢиҖҢжҳҫеҫ—йўҮдёәз–Ҹиҝңз”ҡиҮіиҙҹйқўгҖӮ[27][28] 1815е№ҙеҗҺзҡ„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еҲ©з”ЁжӢҝз ҙд»‘жҲҳдәүд№ӢеҗҺпјҢеңЁеҺҶеҸІеӯҰ家жө·еӣ йҮҢеёҢВ·еҶҜВ·зү№иө–иҢЁе…Ӣзҡ„еӨ§еҠӣжҺЁеҠЁдёӢпјҢ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ҪўиұЎеҸ‘з”ҹиҪ¬еҸҳгҖӮ[29]йӘ‘еЈ«еӣўејҖе§Ӣиў«жҸҸз»ҳдёәвҖңеҫ·еӣҪеҗ‘дёңж–№зҡ„ж–ҮжҳҺдҪҝе‘ҪвҖқзҡ„иұЎеҫҒпјҢ并еңЁеҸІеӯҰдёҠжү®жј”зқҖвҖңеҜ№жҠ—ж–ҜжӢүеӨ«дё–з•Ңзҡ„ж–ҮжҳҺдј ж’ӯиҖ…вҖқи§’иүІгҖӮ[30]зү№иө–иҢЁе…Ӣе°ҶйӘ‘еЈ«еӣҪи§ҶдёәвҖңд»Һеҫ·еӣҪжө·еІёеӨ§иғҶдјёе…ҘйҮҺиӣ®дёң欧д№Ӣжө·зҡ„дёҖеә§еқҡеӣәжө·е ӨвҖқпјҢиҖҢ1410е№ҙеқҰиғҪе ЎдјҡжҲҳдёӯ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ӨұиҙҘеҲҷиұЎеҫҒвҖңиҘҝж–№дё–з•ҢвҖқиҙҘдәҺвҖңйҮҺиӣ®дёңж–№вҖқгҖӮеңЁд»–зңјдёӯ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дҪ“зҺ°дәҶвҖңеҫ·еӣҪжҖ§ж јдёӯзҡ„ж”»еҮ»жҖ§еҠӣйҮҸдёҺдёҘеҺүеҶ·й…·зҡ„з»ҹжІ»ж°”иҙЁвҖқгҖӮ[31] еҸ—еҲ°жіўе…°ж–№йқўеҜ№1410е№ҙвҖңеқҰиғҪе ЎжҲҳеҪ№вҖқиұЎеҫҒжҖ§зәӘеҝө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19дё–зәӘжң«еҫ·еӣҪ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иҖ…ејҖе§Ӣд»ҘвҖңеҫ·ж„Ҹеҝ—е…ғзҙ вҖқеӣһеә”жіўе…°зҡ„зәӘеҝөжҙ»еҠЁ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йҖҗжёҗиў«еЁҒе»үж—¶жңҹжҷ®йІҒеЈ«зҡ„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иҖ…еЎ‘йҖ жҲҗвҖңеҫ·еӣҪдёңйғЁж®–ж°‘иҖ…вҖқзҡ„е…ёиҢғгҖӮзұ»дјји§ӮзӮ№д№ҹдҪ“зҺ°еңЁжҒ©ж–Ҝзү№В·з»ҙжӯҮзү№зҡ„е°ҸиҜҙгҖҠжө·еӣ йҮҢеёҢВ·еҶҜВ·жҷ®еҠіжҒ©гҖӢе’ҢгҖҠжүҳдјҰеёӮй•ҝгҖӢдёӯгҖӮеҺҶеҸІеӯҰ家йҳҝйҒ“еӨ«В·з§‘иө«еңЁ1894е№ҙз”ҡиҮіе®Јз§°пјҡвҖңжҷ®йІҒеЈ«иҜёзҺӢжҳҜз«ҷеңЁйӘ‘еЈ«еӣўеӣўй•ҝзҡ„иӮ©иҶҖдёҠеҙӣиө·зҡ„гҖӮвҖқ[32] йӯҸзҺӣе…ұе’ҢеӣҪж—¶жңҹ з”ұдәҺе°ҶиҘҝжҷ®йІҒеЈ«зӯүең°еҢәеүІи®©з»ҷж–°жҲҗз«Ӣзҡ„жіўе…°еӣҪ家пјҢеј•еҸ‘дәҶи·Ёе…ҡжҙҫзҡ„е®Јдј жҙ»еҠЁпјҢйҮҚж–°е”Өиө·дәә们еҜ№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иҝҷдәӣең°еҢәзҡ„вҖңеҫ·ж„Ҹеҝ—дј з»ҹвҖқи®ӨеҗҢгҖӮдёңжҷ®йІҒеЈ«зҡ„ең°зҗҶеӯӨз«ӢиҝӣдёҖжӯҘеј•еҸ‘дёҺ1466е№ҙйӘ‘еЈ«еӣҪжүҖйқўдёҙеӨ–дәӨеӣ°еўғзҡ„зұ»жҜ”пјҢдҪҝе…¶иў«и§ҶдёәвҖңж–ҜжӢүеӨ«жҙӘжөҒдёӯеҫ·ж„Ҹеҝ—зҡ„е Ўеһ’вҖқгҖӮ[33] 1920е№ҙ7жңҲ11ж—ҘпјҢеңЁйҳҝдјҰж–Ҫжі°еӣ жҠ•зҘЁең°еҢәиҝӣиЎҢзҡ„е…Ёж°‘е…¬жҠ•дёӯпјҢеӣ дёҺжіўе…°зҡ„иҫ№з•Ңдәүи®®еҶіе®ҡдәҶеҚ—йғЁдёңжҷ®йІҒеЈ«зҡ„еҪ’еұһгҖӮеңЁе…¬жҠ•еүҚзҡ„е®Јдј дёӯпјҢеҫ·ж–№еӨ§еҠӣејәи°ғ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вҖңдёңең°дј з»ҹвҖқдёӯ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[34]иЎ—йҒ“еёғж»ЎйӘ‘еЈ«еӣўеҚҒеӯ—еҫҪз« зҡ„ж——еёңдёҺиЈ…йҘ°гҖӮйӯҸзҺӣж—¶жңҹпјҢеӨҡдёӘеңЁдёңйғЁдҪңжҲҳзҡ„иҮӘз”ұеҶӣеӣўпјҲFreikorpsпјүе°ҶйӘ‘еЈ«еӣўз¬ҰеҸ·з”ЁдәҺе…¶иҮӮз« пјҢеҰӮдёңйғЁиҫ№йҳІеҚ«йҳҹдёҺжіўзҫ…зҡ„жө·еҫҢеӮҷи»ҚгҖӮе…¶дёӯпјҢжңҖе…·еҪұе“ҚеҠӣзҡ„еӣҪ家主д№үз»„з»Үд№ӢдёҖвҖ”вҖ”йқ’е№ҙеҫ·еӣҪйӘ‘еЈ«еӣўпјҲJungdeutscher OrdenпјүпјҢз”ҡиҮіеңЁеҗҚз§°гҖҒз»„з»Үжһ¶жһ„е’ҢиҒҢеҠЎеҗҚз§°дёҠе®Ңе…Ёд»ҝж•ҲдәҶ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гҖӮ[35] зәізІ№ж—¶жңҹ еңЁзәізІ№еҫ·еӣҪж—¶жңҹпјҢеҜ№дәҺжқЎйЎҝ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ҺҶеҸІжҖҒеәҰ并дёҚз»ҹдёҖгҖӮжҖ»дҪ“иҖҢиЁҖпјҢжө·еӣ йҮҢеёҢВ·еёҢе§ҶиҺұдёҺйҳҝе°”еј—йӣ·еҫ·В·зҪ—жЈ®е Ўзӯүдәә延з»ӯдәҶ19дё–зәӘзҡ„жӯЈйқўйӘ‘еЈ«еӣўеҪўиұЎгҖӮ[36] йҳҝйҒ“еӨ«В·еёҢзү№еӢ’ж—©еңЁ1924е№ҙжүҖи‘—зҡ„гҖҠжҲ‘зҡ„еҘӢж–—гҖӢдёӯе°ұиөһзҫҺеҫ·ж„Ҹеҝ—дёңеҗ‘移民иҝҗеҠЁпјҢ并и®ҫжғіжңӘжқҘвҖңжІҝзқҖйӘ‘еЈ«еӣўж—§и·ҜвҖқзҡ„еҫҒжңҚи®ЎеҲ’гҖӮ[37]1934е№ҙеёқеӣҪжҖ»з»ҹдҝқзҪ—В·еҶҜВ·е…ҙзҷ»е Ўе®ү葬дәҺеқҰиғҪе ЎзәӘеҝөзў‘ж—¶пјҢеҫ·еӣҪж”ҝеәңе°Ҷд»–еЎ‘йҖ жҲҗ1914е№ҙ第дәҢж¬ЎеқҰиғҪе ЎжҲҳеҪ№дёӯзҡ„зҡҮ家е°ҶйўҶпјҢиҜ•еӣҫд»ҘжӯӨдёә1410е№ҙзҡ„еӨұиҙҘвҖңеӨҚд»ҮвҖқгҖӮ[38] 然иҖҢпјҢеёҢе§ҶиҺұеҮәдәҺе…¶з§Қж—ҸзҗҶи®әи®ҫжғіпјҢиҰҒеҲӣз«ӢдёҖж”Ҝж–°зҡ„вҖңеҫ·ж„Ҹеҝ—йӘ‘еЈ«еӣўвҖқдҪңдёәвҖңеҹәеӣ дј жүҝиҖ…вҖқпјҢе…¶дёӯеҢ…жӢ¬ж–°и®ҫзҡ„зәізІ№йӘ‘еЈ«еӣўе Ўеһ’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Һҹжң¬зҘһеңЈзҡ„йӘ‘еЈ«еӣўеҗҚз§°иў«еәҹйҷӨгҖӮ1938е№ҙ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иў«е®ҳж–№и§Јж•ЈгҖӮ[39]зәізІ№е®Јдј йғЁй•ҝзәҰз‘ҹеӨ«В·жҲҲеҹ№е°”зҡ„е®Јдј жңәеҷЁйҖҗжӯҘеҺӢеҲ¶ж—§жңүдј з»ҹпјҢдёәж–°вҖңйӘ‘еЈ«зІҫзҘһвҖқи®©и·ҜгҖӮ然иҖҢпјҢеңЁйӘ‘еЈ«еӣўж—§ең°дёңжҷ®йІҒеЈ«пјҢе®Јдј жҲҗж•ҲжңүйҷҗгҖӮдҫӢеҰӮеёқеӣҪеӢһеҪ№еңҳ第25еҢәзҡ„ж Үеҝ—д»Қдҝқз•ҷжңүзәізІ№е…ҡеҫҪдёҺйӘ‘еЈ«еӣўеҚҒеӯ—гҖӮеңЁжҲҳдәүдёӯпјҢе…ҡеҚ«еҶӣ第11вҖңеҢ—欧вҖқиЈ…з”ІжҺ·еј№е…өеёҲдёӯзҡ„дёҖж”ҜиЈ…з”ІйғЁйҳҹиҝҳд»ҘйӘ‘еЈ«еӣўеӨ§еӣўй•ҝиө«е°”жӣјВ·еҶҜВ·иҗЁе°”жүҺе‘ҪеҗҚгҖӮ 1945е№ҙеҗҺ1945е№ҙеҗҺпјҢз”ұдәҺеӨұеҺ»дёңйғЁйўҶеңҹпјҢиҒ”йӮҰеҫ·еӣҪзӨҫдјҡеҜ№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еӣһйЎҫе…ҙи¶ЈжҳҺжҳҫеҮҸејұпјҢд№ҹдёҚеҶҚеғҸиҝҮеҺ»йӮЈж ·еҜ№йӘ‘еЈ«еӣўиҝӣиЎҢзҫҺеҢ–гҖӮиҝҷдёҖи®®йўҳеңЁзӨҫдјҡдёҠи¶ӢдәҺжІүеҜӮгҖӮ[40]еҸӘжңүйғЁеҲҶеӨҚд»Үдё»д№үеӣўдҪ“д»Қж—§еқҡжҢҒж—§жңүз«ӢеңәгҖӮ еҫ·еӣҪжөҒдәЎиҖ…з»„з»ҮдёҺеҺҶеҸІз ”究жңәжһ„еҰӮй»‘е°”еҫ·з ”究йҷўд№Ӣй—ҙиҒ”зі»з–ҸиҝңгҖӮе°Ҫз®ЎеҰӮжӯӨпјҢзӣҙиҮі1960е№ҙд»ЈеҲқпјҢдёңж¬§з ”з©¶з•Ңд»ҚжңүдёҚе°‘еӯҰиҖ…иҜ•еӣҫеңЁвҖңеҺ»з§Қж—Ҹдё»д№үвҖқзҡ„еҢ…иЈ…дёӢ延з»ӯдј з»ҹзҡ„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дёҺвҖңдёңзәҝйҳІеҫЎж–—дәүвҖқи®әи°ғгҖӮ[41]иҝҷдёҖзҠ¶еҶөдәҺ1960е№ҙд»ЈеҲқйҡҸеӯҰжңҜд»Јйҷ…жӣҙжӣҝжүҚжңүжүҖж”№еҸҳгҖӮ[42] 1985е№ҙпјҢз»ҙд№ҹзәіжҲҗз«ӢдәҶвҖңеӣҪйҷ…еҺҶеҸІе§”е‘ҳдјҡз ”з©¶еҫ·ж„Ҹеҝ—йӘ‘еЈ«еӣўвҖқпјҢе…¶з ”з©¶е…іжіЁжҖқжғіеҸІгҖҒеҢәеҹҹдёҺ欧жҙІи§Ҷи§’гҖӮ еңЁеҫ·ж„Ҹеҝ—ж°‘дё»е…ұе’ҢеӣҪпјҲдёңеҫ·пјү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д»Қиў«е®ҳж–№и§ҶдҪңвҖңдҫөз•ҘдёҺеӨҚиҫҹзҡ„е Ўеһ’вҖқгҖӮ1985е№ҙзүҲгҖҠеҫ·ж„Ҹеҝ—еҶӣдәӢиҜҚе…ёгҖӢеҶҷйҒ“пјҡвҖңвҖҰвҖҰиҝҷдёӘжІҫж»ЎйІңиЎҖзҡ„йӘ‘еЈ«еӣўеңЁ20дё–зәӘиў«ж”№з»„дёәдё»иҰҒд»ҺдәӢж…Ҳе–„зҡ„ж•ҷдјҡз»„з»ҮгҖӮзӣ®еүҚеңЁеҘҘең°еҲ©дёҺиҒ”йӮҰеҫ·еӣҪд»ҚдҪңдёәдёҖз§ҚзҘһиҒҢвҖ“еҶӣдәӢдј з»ҹеӣўдҪ“еӯҳеңЁгҖӮвҖқ[43] 1991е№ҙ9жңҲ4ж—ҘпјҢиҒ”йӮҰеҫ·еӣҪеҸ‘иЎҢдәҶдёҖжһҡ10еҫ·еӣҪ马е…ӢйқўеҖјзҡ„вҖңеҫ·ж„Ҹеҝ—йӘ‘еЈ«еӣў800е‘Ёе№ҙвҖқзәӘеҝөеёҒгҖӮ[44]еҫ·еӣҪдәҰеҸ‘иЎҢиҝҮд»ҘйӘ‘еЈ«еӣўдёәдё»йўҳзҡ„йӮ®зҘЁгҖӮ йҖҡиҝҮжҷ®йІҒеЈ«зҡ„еӣҪ家иүІеҪ©пјҢйӘ‘еЈ«еӣўзҡ„й…ҚиүІд№ҹй—ҙжҺҘеҪұе“ҚдәҶеҫ·еӣҪеӣҪ家足зҗғйҳҹзҡ„зҗғиЎЈй…ҚиүІгҖӮ жіЁйҮҠеҸӮиҖғж–ҮзҢ®
延伸й–ұи®Җ
еӨ–йғЁйҖЈзөҗ |
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
Portal di Ensiklopedia Dunia